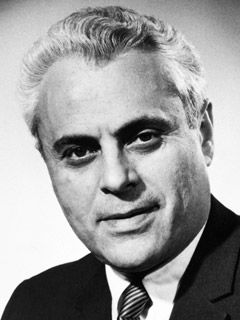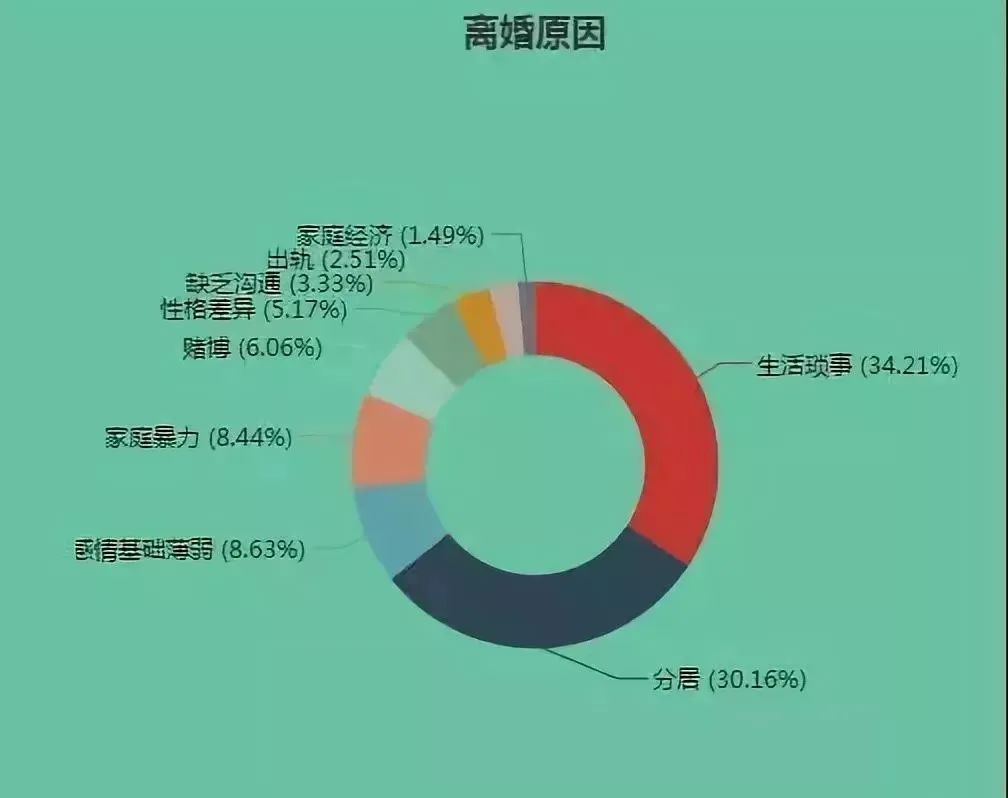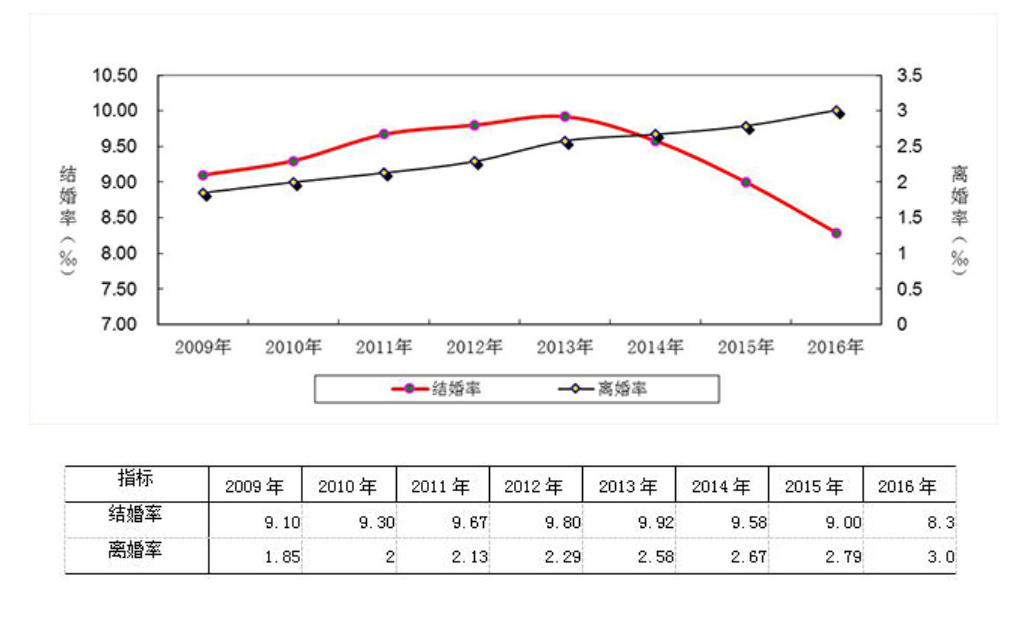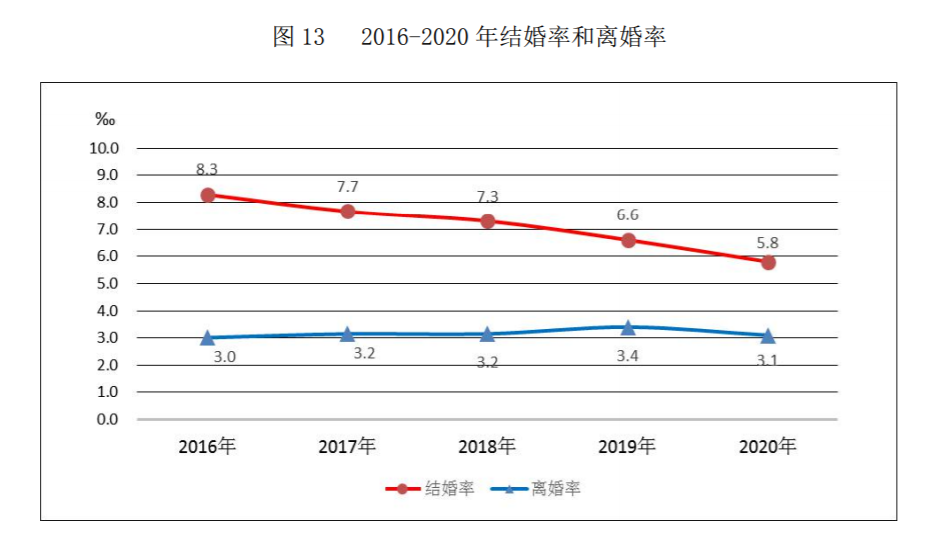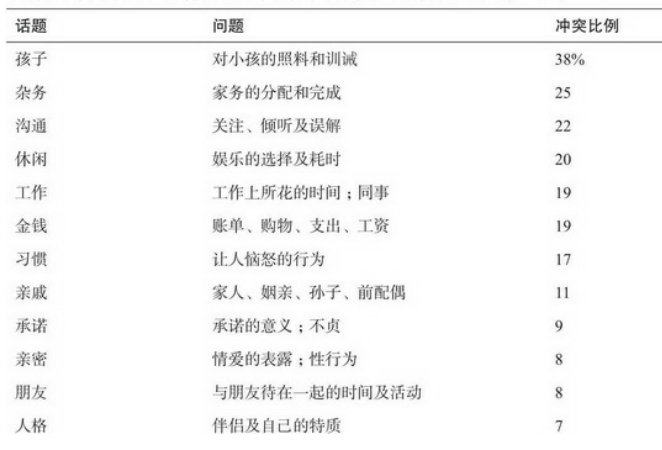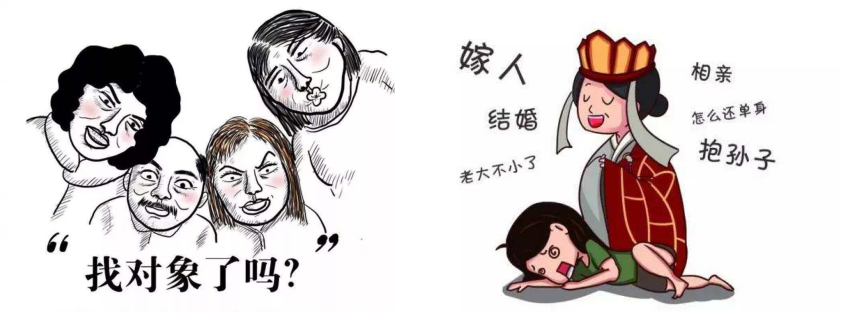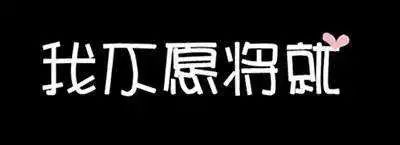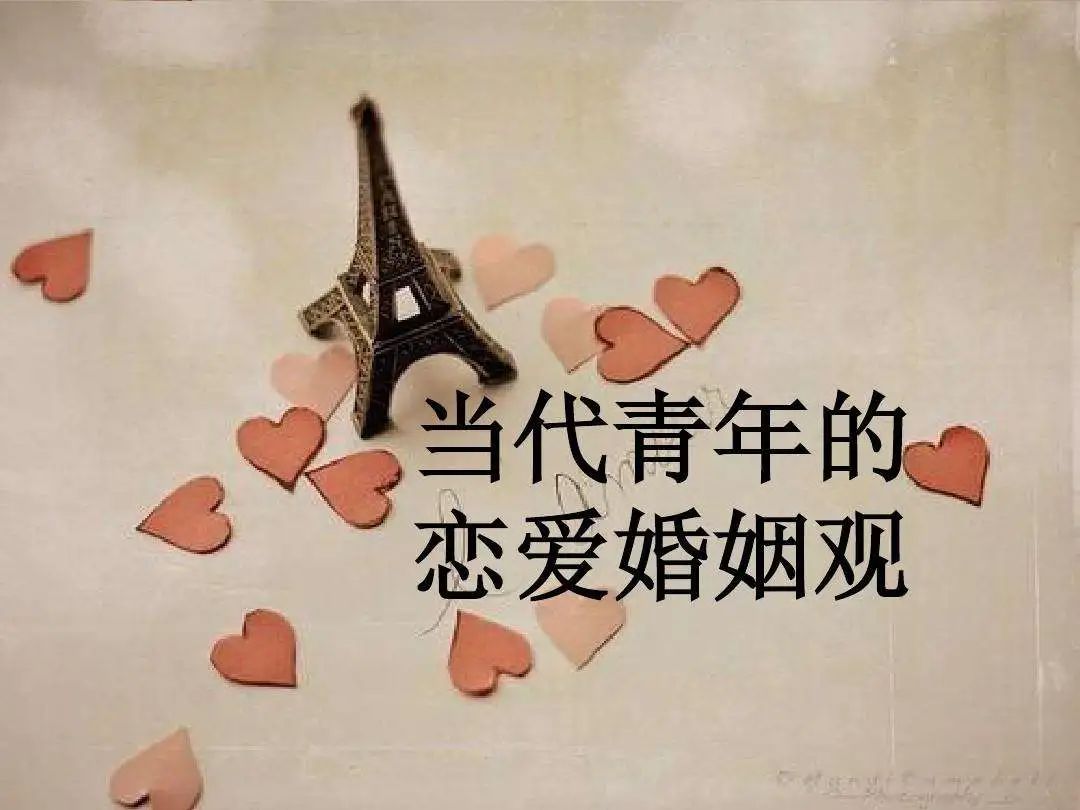婚姻家庭理论 |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Family Life Cycle)
理论整理者 • 殷锦绣
代表性人物及其生平

格利克(Paul C. Glick)
Paul C. Glick(1911-2006)是一位著名的家庭人口统计学家,在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工作了40年,同时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杰出学者和兼职教授。
1933年,Glick在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取得了学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38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1957年撰写的《美国家庭》(American Families)一书、1970年撰写的《婚姻和离婚:社会和经济研究》(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等都是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理论发展历程
Murphy和Staples(1979)总结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时期、扩展时期和修正时期。
家庭生命周期最初的萌芽形成于1903年,Rowntree在对贫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与家庭所处的阶段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在一些特殊阶段,如尚未成年、养育子女、进入老年等阶段,消费大于收人的可能性更大,容易陷入贫困。Rowntree将人的一生按照年龄从出生到死亡分成9个阶段,并分析贫困产生的差异性。这种划分方法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家庭的生命周期,而是依照个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的划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初创时期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上是将个人生命历程,或者家庭子女生命历程与家庭夫妻关系混搭的一种研究模型。但把家庭的重大事件对个人从贫困一不贫困之间转换的分析思路,直接影响到后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所以,在所有的家庭生命周期分析中,事件(event)和转换(transit)都是最为重要的指标。
在初创时期之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发展被更多的学者扩展和完善。除了正式提出者Glick之外,杜瓦尔(Duvall)和希尔(Hill)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Glick第一次提出了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被社会人口学家们视为最基础和传播最广泛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Glick认为,家庭生命周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包括初婚、第一个子女出生、最后一个子女出生、第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最后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结婚)、配偶一方死亡、残存一方死亡等七个事件,并将家庭生命周期按照核心家庭的历史,从结婚至配偶死亡导致解体划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六个阶段。这种简单明晰的划分方法,不仅给出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性的划分,而且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每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能够适用于当时美国核心家庭的变化过程,由于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计算性,更为社会人口学家们所使用。
但这一理论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如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重视子女年龄的变化,而是以子女出生子女结婚或者子女离家为主要代表。
几乎与Glick同时,在1946年 Duvall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四阶段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但这一成果在Glick之后的1948年才得以发表。随后,Duvall和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四阶段模型扩展为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1964年,Hill将家庭生命周期七阶段模型扩展成为九阶段模型。与Glick的七阶段模型集中在按照妇女年龄的家庭生命周期事件的转折点不同,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更加注重家庭中子女的成长过程,更为强调子女年龄的变化,也更多地承袭了社会心理学的传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大家更多承袭了 Duvall和Hill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经过Glick、 Duvall和Hill对家庭生命周期的梳理和阐述,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已经比较完整,应当说基本可以作为完整的论框架或者模型用于家庭研究之中。后来的学者在Glick、Duvall和Hill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各种更为精细的分方法。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生命周期类型产生了很大变异,传统的家庭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有所变化。比如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的现象,以及离婚和单亲家庭数量的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或者是即便结婚了也不生子女。这些变化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中原有的只能应对初婚家庭的概念明显不合时宜,也因此诞生了许多更适应新时代及不同文化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即此时进入了修正时期。Murphy和 Staples(1979)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Rogders在1962年提出的10阶段、Wells和Gubar在1966年提出的9阶段、Duvall在1971年提出的8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而在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最初推演主要集中在台湾的学者,杨静利和刘一龙(2002)将台湾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描述为未婚、有偶无子女、有偶有子女、死亡四个阶段;而大陆学者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对中国解释力有限(吴兴旺, 1999),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类型太复杂,一些家庭很难归于某一生命周期阶段,因此有学者按照自己研究分析的目的和需要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姬雄华, 2008)。
代表性著作
1.Carter, H., & Glick, P. C. (1970). Marriage and Divorc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Glick, P. C. (1957). American Families. Russell & Russell.
理论观点
不同研究者提出的模型阶段也不同,但无论划分为多少个阶段,总体的观点原则都是这样的:
1.所有家庭都随时间而变化。有些变化是可预测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2.每个阶段都有其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只有较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家庭才能顺利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3.家庭危机更容易在家庭阶段转变的时候出现;
4.家庭生命周期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特殊性。
研究方法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研究数据和方法上也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从研究数据而言,最初的家庭生命周期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横断面的数据,有的甚至是一个较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这种数据一般只能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简单的划分和描述,无法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和原因。
后来的研究者数据使用有比较大的改善,他们开始使用多期的横断面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就能够刻画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过程,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从一个断点性和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变为能够适用于家庭变迁方面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分析框架。 Lansing和Kish(1957)就家庭生命周期模型与单一使用年龄分组模型检验了个人的六个不同经济特征,他们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比年龄分组模型更有解释力,因为家庭生命周期中包含了更多的个人角色内涵。故家庭生命周期完全可以像年龄等变量一样,作为一个自变量来使用。
在数据使用方面,Glick本人不但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而且使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加以分析,并根据变化,更新了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性延续时间的变化。当然这样与他本人在人口普查局工作,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这些数据有关(Glick,1977)。
研究证据
修正后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给家庭社会学家、消费和市场研究者等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Montgomery和Sore(1997)使用爱情态度量表测量了250个成人样本,并按照他们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四组:大学年龄的单身青年人、已婚无子女青年人、已婚有子女成年人、已婚子女离家的成年人,发现在四组人群之间关于爱情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发现没有结婚的青年人比已婚人群对爱情的态度更富有热情,而有子女的成年人则更为含蓄。
Fritzsche(1981)综合使用了 Murphy和 Staples以及Wells和Gubar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发现年轻单身家庭的能源消耗,特别是天然气消耗是最少的在有子女已婚中年家庭能源消耗是最多的,特别是汽油、木材和燃煤。而在随后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中,能源消耗会逐渐降低。
McLeod和Ellis(1983)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的分类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家庭户的住房消费模式,特别是人均住房消费情况,因为家庭发展不同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子女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房间来做婴儿房和游戏房,故在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需要更多额外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