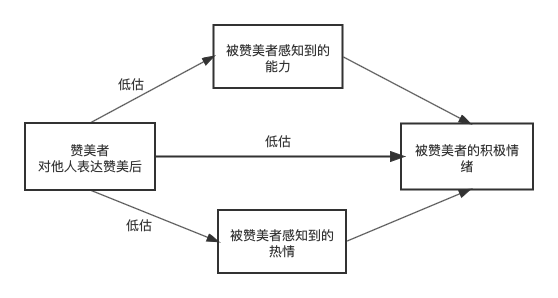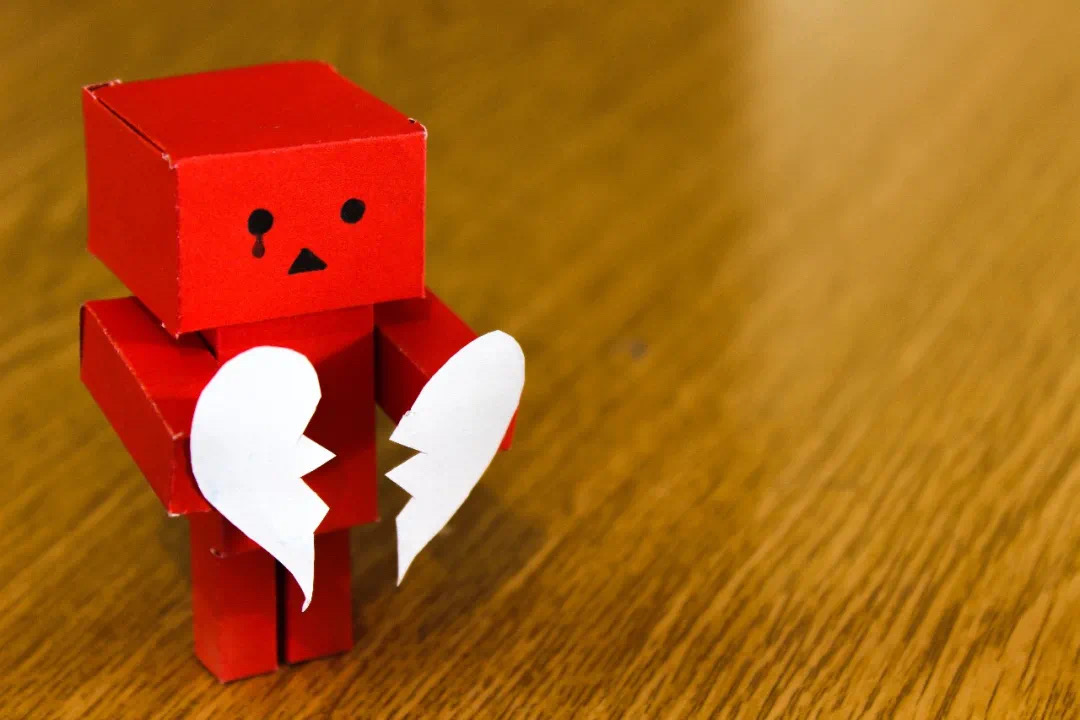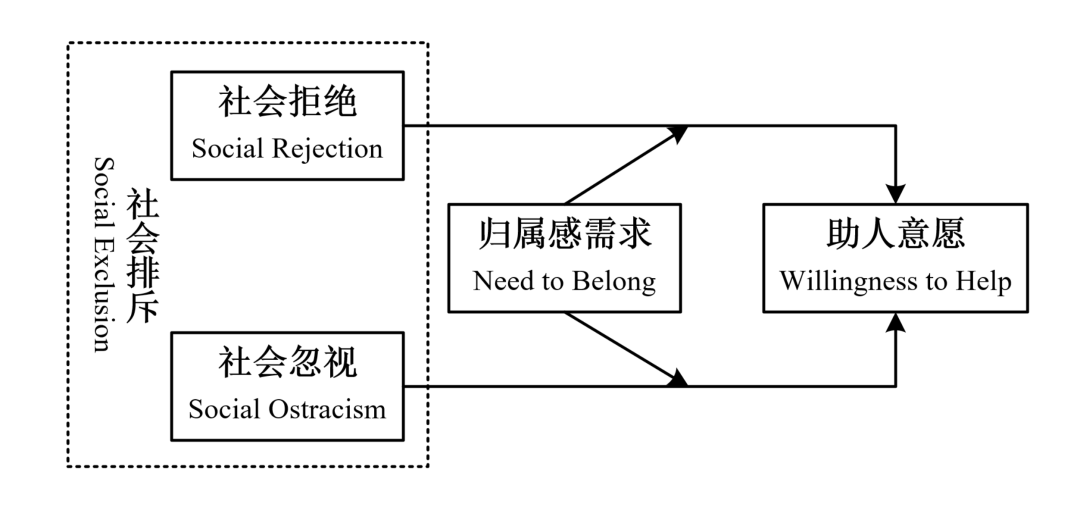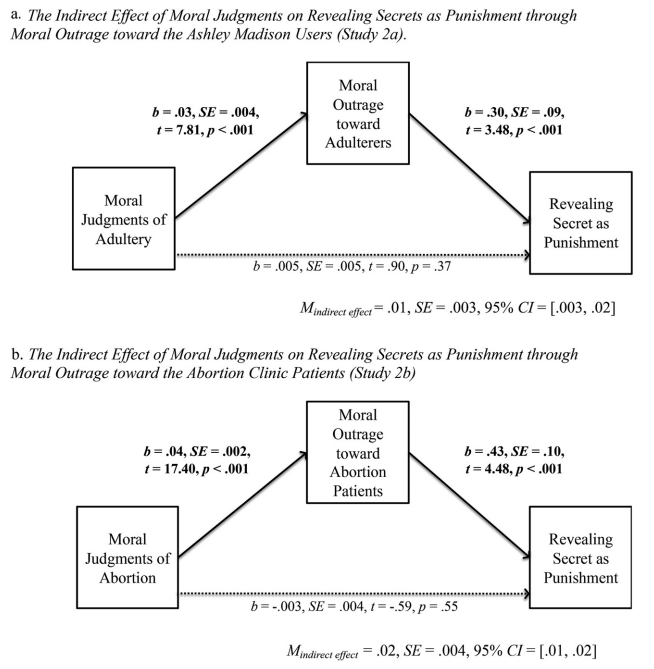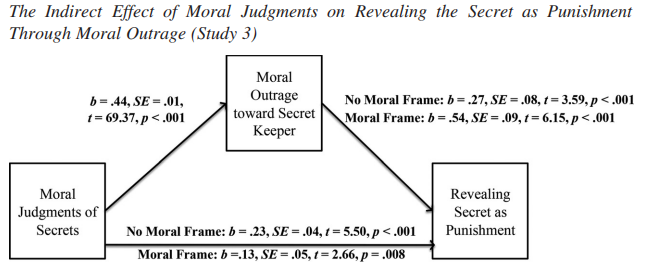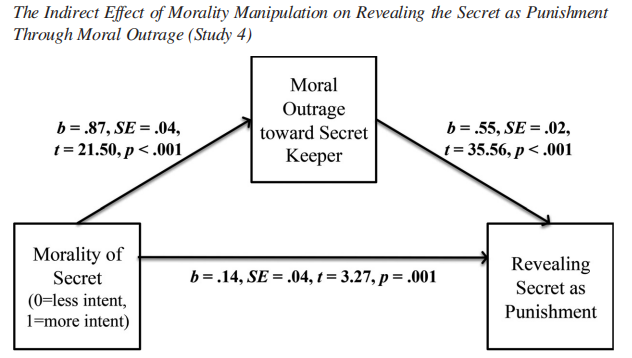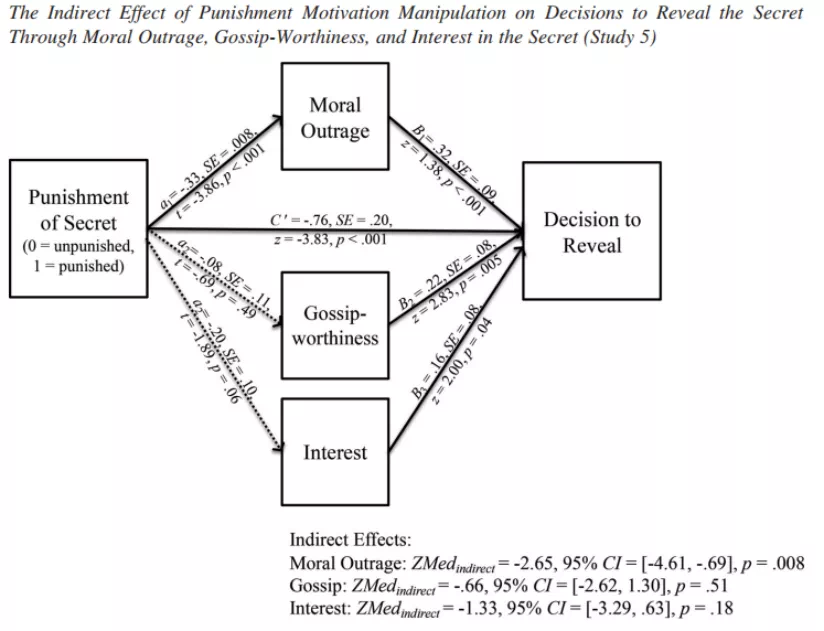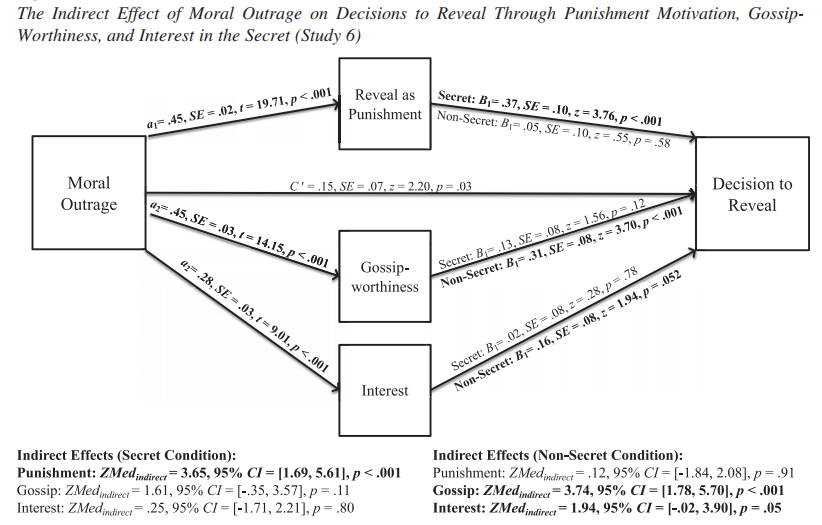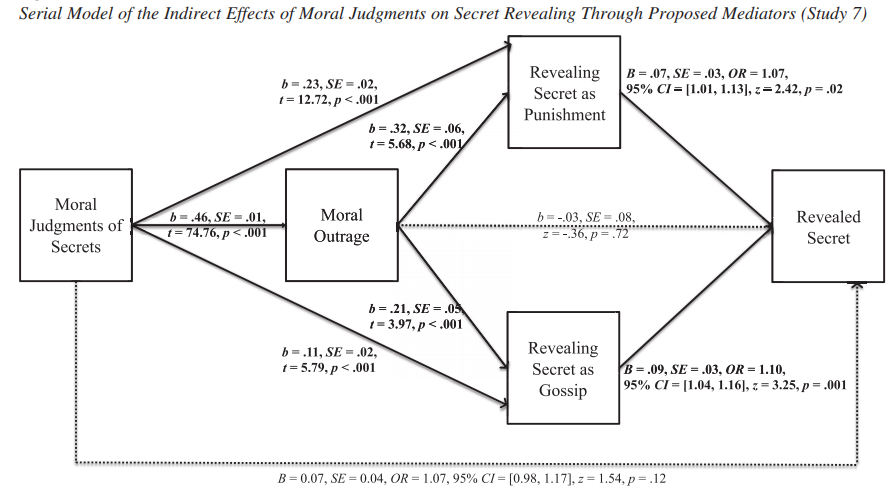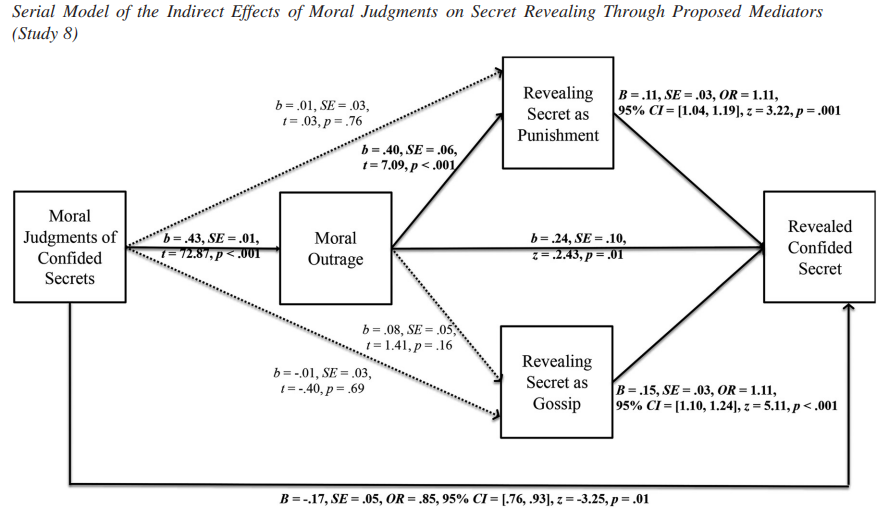不是吧,这样也能变聪明...
作者|姜林屾
最近,一位朋友神情忧虑地向学堂君诉苦:
这周钥匙已经丢了2次,组会报告的PPT检查了几遍还是有拼写错误,最尴尬的是,我想跟新来的小哥加微信好友,结果拿出手机直接打开了收款码……你说我是不是失了智啊!
说起记忆衰退、注意力涣散、精神恍惚等状况,不免让人心中一紧。当前,越来越多年轻人受工作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出现一些病理或非病理性认知功能下降的症状。
这其中,执行功能下降是最重要的症状之一。

(图源网络,侵删)
变“聪明”的关键因素: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包括三个核心成分: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1]。
其中,「工作记忆」是个体对信息进行短暂保存与调用的能力,“过目不忘”的人就是工作记忆能力极强;
「抑制控制」是指个体可以克服强烈的内在倾向和外在诱惑去做更适合或更需要的事的心理过程,如抑制控制受损的儿童在知道会被批评的情况下仍然控制不住上课打闹;
「认知灵活性」则是指个体可以从一种优势反应转化到另一种适应情景的反应中去,如在卡片分类任务中,认知灵活性好的个体可以快速适应不同分类规则(比如先按颜色、再按形状)。
而执行功能便是个体有效控制思维与行为来达成目标的一种复杂的高级认知功能。如果将执行功能比作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那么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就是三个核心部门,执行功能需要恰当地统筹协调各部门进行分工合作以达到目标。
一个公司要顺利达到运营目标,需要主管和各部门都给力才行。而一个人的认知功能良好、行为表现“聪明”,离不开执行功能及其核心成分的高效运转。
研究指出,更好的执行功能与更优的学业成绩、事业成功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显著相关[2-3]。

(图源网络,侵删)
看到这你可能也想到,要抵抗失智变更聪明,提升执行功能不就好啦!
研究者也这么想,于是干预执行功能的研究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研究者们尝试了各种干预方案,最后,将179项涉及各类干预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比较[4],结果发现——
惊!“佛系”运动效果超好
按捺住好奇的心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往研究的结果。
在研究初期,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单领域认知干预的实验:比如先对参与者的工作记忆水平进行测试(前测),然后针对工作记忆进行训练,几周之后再去测试参与者的工作记忆表现(后测),结果发现,这种干预的确可以提升参与者的工作记忆测试成绩[1]。
但是,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指出,单领域的认知干预训练总是在刺激类型和反应要求上保持不变,具有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这样一来,密集的训练只能锻炼到被试对特定领域的答题策略,而难以实现像提升执行功能这种综合能力的干预目标[5]。
单领域干预效果的稳定性和可迁移性有限,或许综合多领域的干预方案更能达到预期效果?
于是,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综合性干预方案,如体育锻炼和正念冥想。结果发现,普通有氧和无氧运动可以增加身体协调性、提升抑制控制能力[6],而持续8周的冥想静坐可以减轻压力、提升选择性注意能力[7]。
不过,单独进行体育锻炼或冥想训练对执行功能的影响,都不如一种“佛系”运动——身心结合的正念型运动干预效果好。
正念(mindfulness)源于佛教核心的禅法,也被称为“内观禅”,其内涵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以及不做评判[1]。
20世纪70年代,乔卡巴金等学者关注到“正念”这一东方概念,在进行系列科学研究后,将其改良整合为了现代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技术之一,并由此诞生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等心理疗法,在焦虑、抑郁、慢性疼痛治疗乃至亲密关系咨询领域广泛应用。
正念和运动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创造性实践,具体的正念型运动有瑜伽、中国传统运动如太极和气功等。
所有正念型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保持情绪平静和注意力集中,抑制内部和外部分心,使一个人保持完全“在场”的状态。
研究者归纳总结了39项涉及正念型运动的研究,涵盖了学龄儿童、青年和老年人各年龄层群体,其中37项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正念型运动对执行功能的积极影响[1]。
//瑜伽
瑜伽从印度梵语而来,其含义为“一致”或“和谐”。现代瑜伽是指一系列包含各种体式的身心互动法,需要调动参与者的柔韧性、平衡力、呼吸法和正念冥想能力。令人惊喜的是,瑜伽对于执行功能的三项核心成分——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都有提升作用。

(图源网络,侵删)
一项针对12岁儿童的干预研究发现,坚持完成4周瑜伽训练后,儿童在当下表现出更好的抑制控制能力[8];而一项以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的10周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完成瑜伽训练的个体报告了更少的压力,并在任务中表现出更好的认知灵活性[9]。另一项干预研究邀请了平均年龄为75岁的老人,在后测结果中发现,参与瑜伽训练的老人在记忆力、抑制控制能力、言语能力方面的积极变化显著多于没有参与训练的同龄老人[10]。
看来不管哪个年龄阶段,在把握自己身体能力范围的前提下进行瑜伽练习,都能从中获益!
//中国传统运动:太极和气功
太极和气功根植于中国人的心身实践,它们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避免挣扎或控制自己的思想,试图强行行事被视为适得其反,让一切顺其自然发生,以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体育锻炼,太极和气功这类传统运动需要更高程度的心理意识和自我控制。不仅是国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近期科学研究结果也发现,这类传统运动对执行功能的确大有好处。
针对平均年龄为12岁的儿童研究发现,在坚持了4周的训练后,学习气功的儿童在计划和抑制控制力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学习西方放松锻炼方法的儿童[11]。另一项研究将60-84岁的健康老人随机分组,进入太极班或其他有氧、无氧和柔韧性锻炼课程,在6个月的干预后,太极组的老人在记忆力和言语流畅性上都表现出显著优势[12]。
想不到,公园里每天坚持打太极、练气功的大爷大妈是一波修身养性健身健脑的隐藏王者。下次感叹完“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的精神气魄和体力劲儿后,不如主动加入锻炼!

(图源网络,侵删)
生存智慧:找回连接
大量研究表明,压力会损害执行功能,长期的压力让大脑变得更糟[13]。若当我们频繁感到自己“失了智”,或许这正是身体和大脑在发出“过劳”警告。

(图源网络,侵删)
正念型运动可以减少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并降低生理层面的应激水平,将身心都带入一个自然与和谐的状态,可谓是融合了正念和运动各自的优势,并达到1+1>2的效果。
这反映了这样一种生存智慧:在信息爆炸、压力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漩涡中,专注内心的声音、找回与身体的连接,以此拥有更多面对世界的能量,让自己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下一次,脑子离家出走怎么办?想变聪明怎么搞?
不妨试试正念型运动这味特效药!
参考文献:
[1]Diamond, A. & Ling, D. S. (2019).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and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efforts to improve executive functions, including working memory. In J. Novick, M.F. Bunting, M.R. Dougherty & R. W. Engle (Eds.), Cognitive and working memory training: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pp.143-43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Alloway, T. P. , & Alloway, R. G. . (2010). Investigating the predictive roles of working memory and iq in academic attainment. J Exp Child Psychol, 106(1), 20-29.
[3]Bailey, C. E. . (2010). Cognitive accuracy and intelligent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brain and in business. Ann N Y Acad, 1118(1), 122-141.
[4]Hughes, C., & Dunn, J. ( 1998). Understanding mind and emotion: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state talk between young friends. Dcwloprnrntal Psycliol, 34(5), 1026-1037
[5]Moreau, D., & Conway, A. R. A. (2014). The case for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cognitive training. Trends Cogn Sci, 18(7), 334-336.
[6]Schonert-Reich, K. A., Oberle, E., Lawlor, M. ·S., et al. (2015). Enhancing cognitive an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simple-to-administer mindfulness-based school program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ev Psychol, 51(1), 52-66.
[7]Jensen, C. G., Vangkilde, S., Frokjaer, V., et al. (2012). Mindfulness training affects attention-or is it attentional effort? J Exp Psychol, 14(1), 106-123.
[8]Manjunath, N. K., & Telles, S. (2001). Improved performance in the Tower of London test following yoga.Indian J Phys Phar , LJ5(3), 351-354.
[9]Bilderbeck, A. C., Farias, M., Brazil, I. A., et al. (2013). Participation in a 10-week course of yoga improves behavioural control and decreas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 prison population. J Psychiatr Res,47, 1438-1445
[10]Hariprasad, V R., Koparde, V, Sivakumar, P. T., et al. (2013).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yoga-based intervention in residents from elderly homes: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dian J Psychiatr, 55, S357.
[11]Chan, A. S., Sze, S. L., Siu, N. Y., et al. (2013). A Chinese mind-body exercise improves self-control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LoS One, 8(7), e68184
[12]Taylor-Piliae, R. E., Newell, K. A., et al. (2010). Effects of tai chi and Western exercise on phys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healthy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J Aging Phys Act, 18, 261-279
[13]Arnsten, A. F. T., et al. (2015). Stress weakens prefrontal networks: Molecular insults to higher cognition. Nat Neurosci, 18, 1376-1385.
作者 | 姜林屾
编辑 | 水金z
美编 | Zene
(本文由京师心理大学堂原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联系「京师心理大学堂」微信公众号后台,征得同意后方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