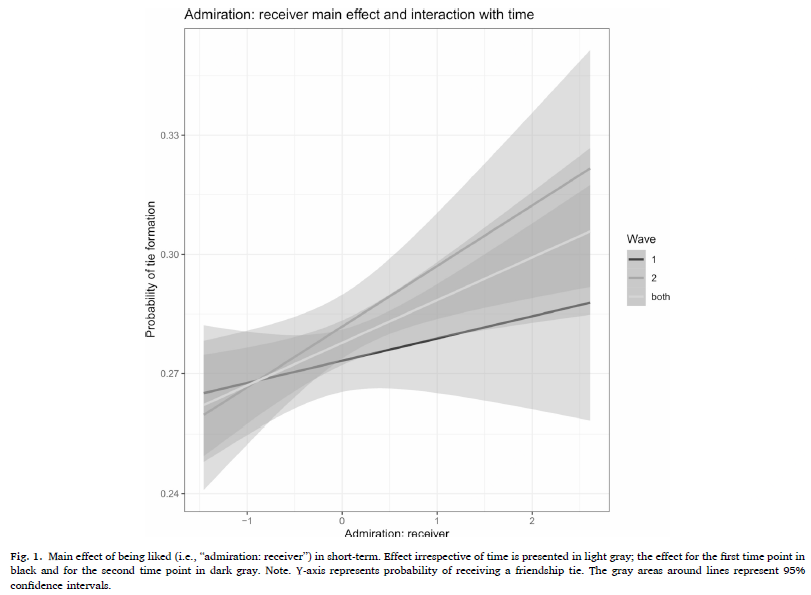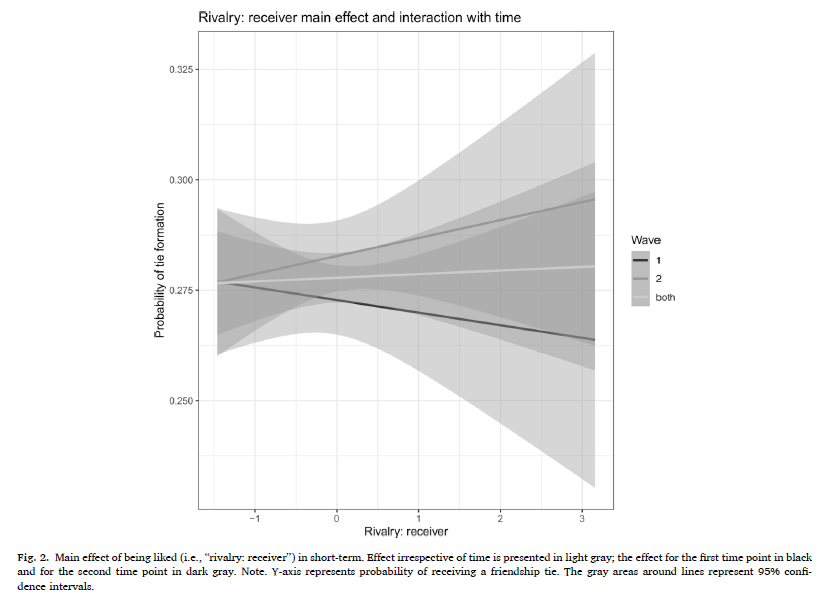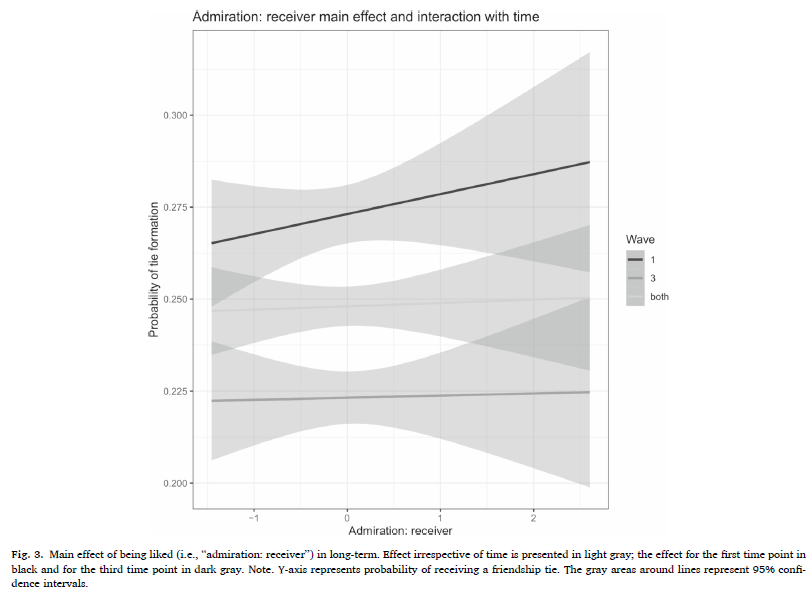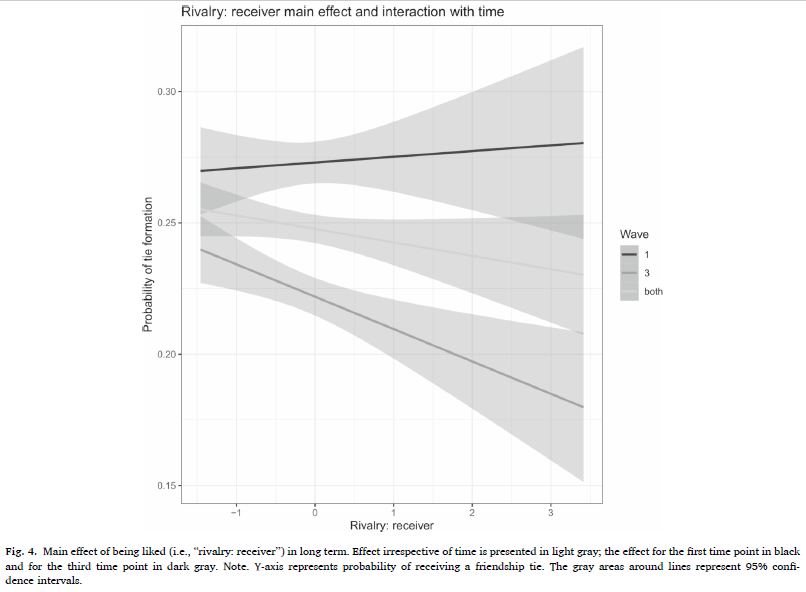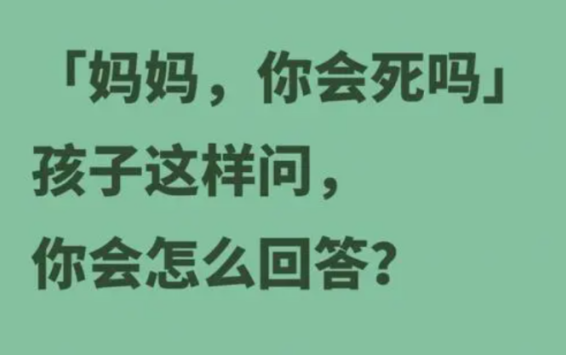「中国式母女关系」:是什么让我们相爱相杀?
本期作者 高文洁
提到中国式母女关系,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
青年导演杨明明给出的答案是「控制」与「反叛」,在她的电影《柔情史》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女儿刚到饭桌前坐下,母亲说:“你以后要再起得这么晚,我真就不管你饭了啊。电饭锅要一直插着电给你保温,你从来都不考虑这些。”女儿忍不住拌了几句嘴,扒拉了几口饭之后,母亲又纠正道:“人在饭桌上永远不能这么吃饭,端不住饭碗。”听到这里,女儿不说话了,一边把放在桌上的饭碗端起来,一边用眼睛瞪着母亲,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导演在她的自述中谈到这些戏:
「“吃”象征了母亲的控制欲。很多人都问电影里是不是我和我妈的关系,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表现的这种关系逻辑,母女之间互相看不顺眼又离不开彼此,相爱相杀,想做到既不侵犯又不疏远,实在太难了。」
我们习惯于描述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式的母爱,一种不可否认的柔情,也是无法拒绝的枷锁。我看过许多对母女关系的探讨,直到读到结构派家庭治疗的「缠结型关系」,我才意识到——母女关系的拧巴与对抗,或许需要放到系统的层面去理解。
01
什么是「缠结型关系」?
在缠结型关系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人际界线(boundary)?
结构派家庭治疗师Minuchin(1974)认为,人际界线是一种管理家庭成员之间物理和心理距离的规则,它调控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例如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父母总是介入去解决孩子们之间的争论,那么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界线就受到了侵蚀,孩子们就很难学会如何为自己辩护。
家庭中的界线(boundary)有三种类型,分别是:
清楚的界线(正常关系):一个清楚的界线可以使子女与父母之间保持互动,但又把孩子从夫妻亚系统中排除开来。
僵硬的界线(疏离型关系):在一个家庭成员有需要的时候,疏离型关系的家庭成员不会给予支持。
混乱的界线(缠结型关系):边界混乱而相互依赖,缠结型母亲(或父亲)会侵入孩子的生活,阻碍孩子的发展和干扰他们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
所谓的「中国式母女关系」,常常映射的就是这最后一种家庭关系模式。
我想到前几天有一条点赞16.2万的微博,朋友转发给我说:“这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微博大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下节选自微博内容):
家里人给表妹做了一碗牛肉面,表妹刚喝了两口汤,家里人说:
“你加点辣椒油。”
表妹说好,她一会再加;刚吃一口面,家里人又说:
“这个辣椒油看着辣,其实不辣的。”
……
经过几次三番的劝说,表妹勉强拿起勺子盛了辣椒油,家里人急忙说:
“你盛红油,把那些辣椒料去掉,油才香啊……欸对,你重新盛……不是不是,你贴着表面才行,勺子给我,我来。”
在我朋友(作为一个女儿)的视角里,每当她被这样悉心照料,她都感到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她的确「受益」于这样的关系;另一方面,真实的情感和自主性被「为你好」所阻碍而无法表达(Love,1990),她又会因此感到抑郁和焦虑。
那么,为什么母亲和女儿会这样无法摆脱地缠结在一起?
02
对父亲的「恨」共筑了母女的缠结
在大多数刻画东亚母女关系的电影里,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杨荔钠导演的《春潮》,还有美国去年新上映的《瞬息全宇宙》,父亲都处于一个「缺席」的位置。
某种程度,撇开父亲角色来探讨母女关系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因为不论这位父亲是否与母女共同生活,他的角色、身份,都会活在母女的日常对话当中,影响着母亲和女儿,包括她们共同关系的发展轨迹。
看到一个「缺席」的父亲,才能理解「缠结」的母女。

Minuchin曾提到一个他经常遇到的家庭模式,他称之为“缠结的妈妈-疏离的爸爸”综合征,也就是说,缠结与疏离是相互的。
当一对父母无法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父母的一方就会将焦点转移到孩子身上,通常母亲与孩子更容易亲近,也更容易将孩子拉拢为自己的“同盟者”。
母亲可能会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以降低夫妻冲突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寻求孩子的安慰与帮忙,与孩子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父亲。而达成“家庭联盟”的过程,常常伴随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抱怨、批评或贬低。换句话说,母女之间的“缠结”与父亲的“消失”是同时发生的。
电影《春潮》对这种联盟对抗进行了艺术性的呈现:
母亲坚持认为自己曾经的丈夫(女儿的父亲)是一个“流氓”,即使离开多年,也常常在女儿面前指责对方。有一次在饭桌上,女儿提到:“我爸脾气是挺好的。”母亲立刻讥笑了一句:“哪里好啊。”

接着问女儿:“你说来听听看。”
没等女儿回答,又自顾自说道:“就会装老好人,其实是啥人,你是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啊。”
这部电影的处理是有些病态化的,但它能让我们窥到,当父亲远离家庭,母亲抱怨父亲,孩子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又怎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家庭的保护神」,去“平衡整个家庭的力量”。
一项发表在Child Development上的调查研究发现,孩子年龄在3至22岁的家庭中,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介入所有家庭纠纷(除了婚姻冲突),而当孩子作为第三方介入到家庭矛盾时,他们通常使用分散注意力的策略(Vuchinich,1988)。
母亲分散了自己的焦虑,但却从情感上削弱了这个孩子;孩子在自我选择空间变少的同时又会滋生出叛逆和反抗。这或许正是女儿与母亲之间既相互怜悯又相互斗争的矛盾症结所在。
03
为什么这种缠结不是“爱”的体现?
或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这种“缠结”不是母爱的体现,这种“联盟”它为什么不能代表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凝聚力呢?
Manzi(2006)对缠结型关系(Enmeshed relationship)和家庭凝聚力(Cohesion)进行了区分,研究者认为它们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凝聚是指整个家庭功能健康完好,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关爱、分享,这种健康功能还包括适应和设置清晰的家庭界线;而缠结型关系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母亲与女儿之间过度亲密,隔绝了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并且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女儿的「亲职化」,让本该站在“孩子”位置上的女儿,站到了配偶甚至是父母的位置上。
《The Emotional Incest Syndrome》的作者Patricia Love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缠结型关系包含两个特征:一是母亲会“利用”孩子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二是母亲会“忽略”孩子的很多需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呈现母女关系的作品中——
她代替了丈夫的陪伴与亲密。她代替了母亲的母亲照料生活起居。甚至,她代替了她某一方面缺憾的人生。

我不想否认,母女之间拥有可能其他任何亲属都无法复制的微妙关系,这篇文章也只是切开了母女关系的某一个剖面。
只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去改变母亲、去改变自己,或者在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上来回争执而无果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母女关系的小齿轮是怎样在更大齿轮的推动下艰涩运转的,我们是不是能换一个用力的方向?
这不是“母亲”或者“女儿”的错,系统层面的改变或许能让我们彼此都轻松一点。
家姻心理最早是1996年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婚姻家庭研究与治疗中心,该中心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婚姻家庭研究、专业咨询师培训、以及面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与心理咨询机构。
家姻心理致力于为婚姻家庭、婚姻家庭咨询师和相关机构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致力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面向婚姻家庭、咨询师和相关机构的心理健康服务产品,提升我国婚姻家庭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
我们长期与北京师范大学方晓义教授及其团队合作,并在其指导下研发产品。所有研发人员均为婚姻家庭或心理学领域硕博士毕业生,具备多年从事婚姻家庭或者心理学领域教学、科研和应用服务的经验。
参考文献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Family Therap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ve, P. (1990). TheEmotional Incest Syndrome: What to do When a Parent's Love Rules Your Life. Bantam.
Vuchinich, S., Emery, R. E., & Cassidy, J. (1988). Family members and third parties in dyadic family conflict: Strategies, alliances, and outcomes. Child Development, 59(5), 1293-1302.
Manzi, C., Vignoles, V. L., Regalia, c., & Scabini, E.(2006). Cohesion and Enmeshment Revisited Differentiation, Identity, andWell-Being in Two European Cultures. Journal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673-689.
迈克尔·尼克尔斯, 西恩·戴维斯. 家庭治疗:概念与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长期在母亲「控制」之下,女儿会变成什么样.人物杂志.2019.
策 划:高文洁
撰 稿:高文洁
编 辑:崔 琪
美 编:郭雨馨
图源 | 电影《柔情史》《春潮》《瞬息全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