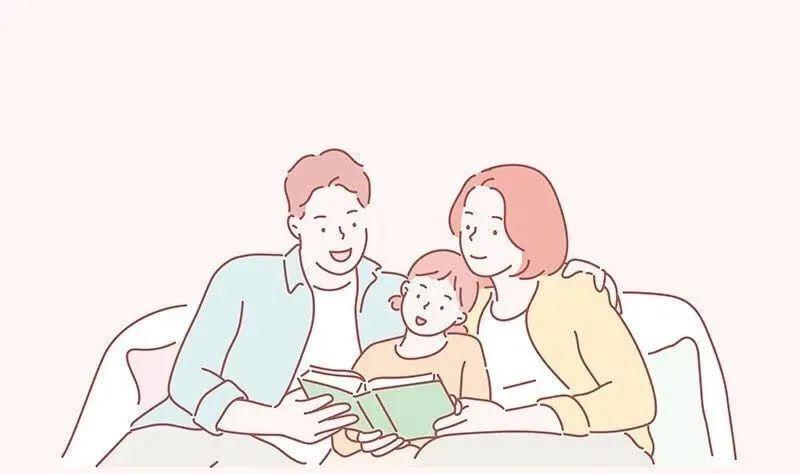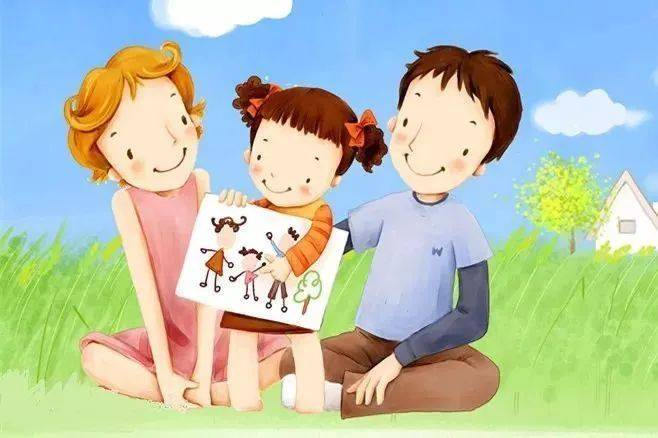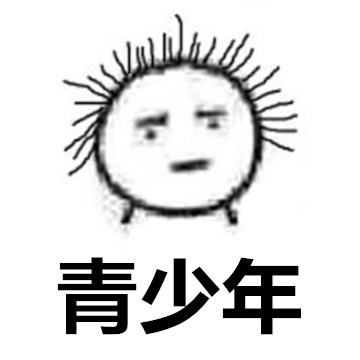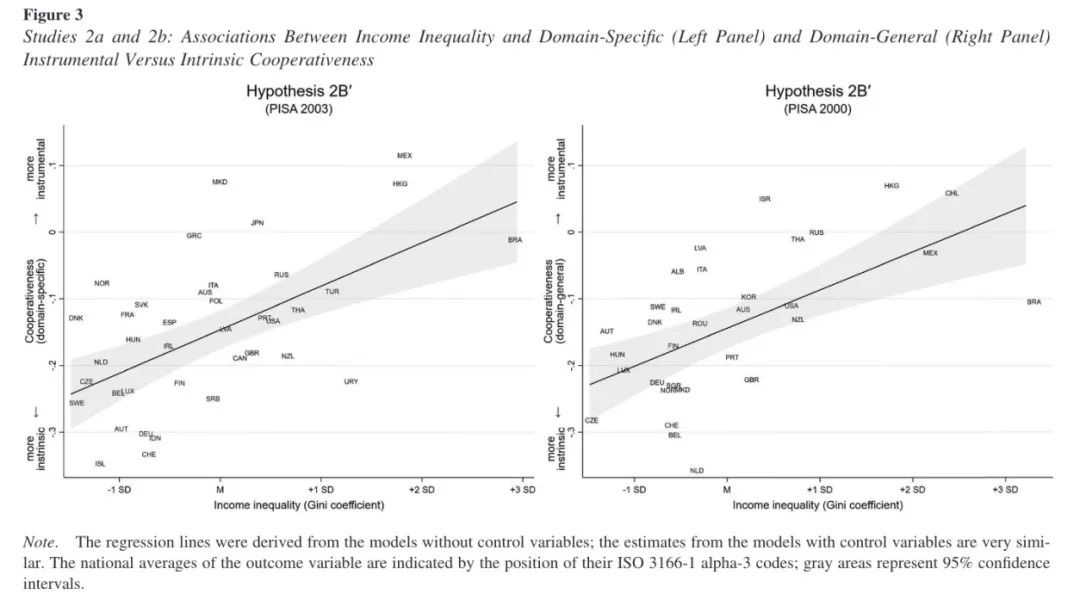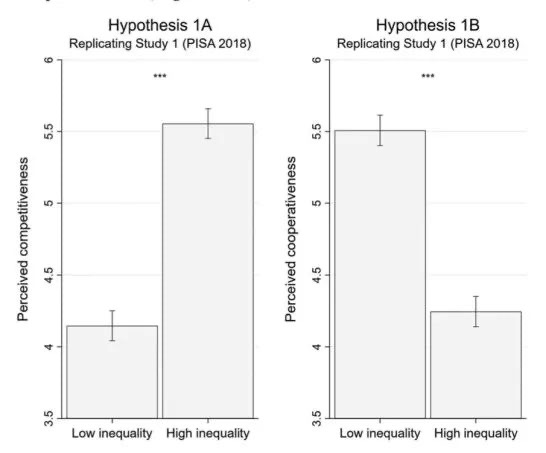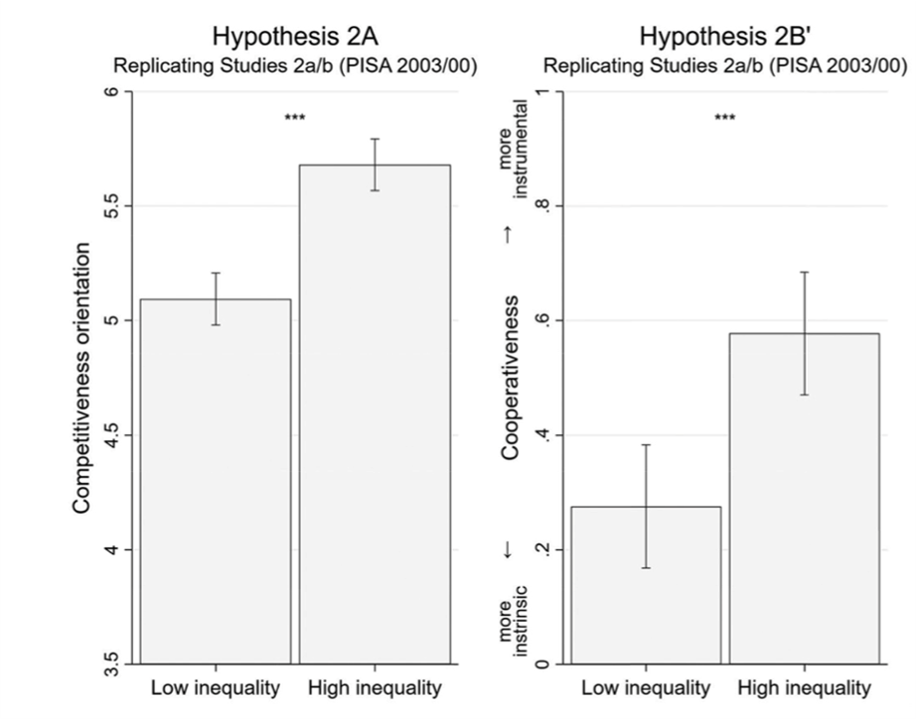心理视角 | 如何帮助孩子学会调节情绪?
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
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本期作者
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级本科生。喜欢排球、秋日和温暖有力的文字。
请大家现在开始在头脑中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某天孩子放学回到家,皱着眉头苦着脸,父母想知道孩子怎么了,刚刚开口说了一两句话孩子便开始放声大哭。
1
帮助孩子认识情绪
上述四种选择分别对应了中国父母的四种元情绪理念:情绪不干涉、情绪教导、情绪摒弃以及情绪紊乱(叶光辉等, 2005)。具有不同元情绪理念的父母会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情绪教育策略,进而影响孩子情绪能力的发展。
研究发现,具有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消极情绪时能给予包容和温暖的情绪反应,并能教导孩子积极应对情绪,促进孩子情绪能力的发展(Gottman et al., 1996;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而其余三种元情绪理念则对孩子的情绪能力及其他社会化行为的发展无益。
拥有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能敏感觉察自己和孩子的情绪,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反应,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情绪感受,并与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题(Liang et al., 2013)。
那么,父母该如何践行情绪教导理念,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0~12岁的孩子常常通过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由于情绪是一种复杂且较为抽象的身心体验,年龄较小的孩子的认知水平尚未发育完全,当遇到诱发情绪的事件时,他们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用原始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哭闹、扔东西等。
其次,父母可以尝试通过询问的方式来确认诱发孩子行为的情绪。例如:“同学误会你拿走了他的铅笔,你是不是感到委屈、难过,所以哭了?”这样不仅能让孩子知道自己哭泣背后的原因,还能学会具体描述情绪的字词。
2
引导孩子表达情绪
当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采用某些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以释放强烈情绪带来的身体紧张感。针对低年龄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父母需要引导孩子,让孩子明白:情绪的出现并不是问题,如何表达情绪才是关键。在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情况下,适当地呐喊和运动等方式都可以起到发泄情绪、缓解紧张的作用。
除了用行为发泄情绪外,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言语来表达情绪。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用言语表达消极情绪能让孩子更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采取更理智的反应。这个表达的过程不仅能锻炼孩子的思维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能使孩子学会用恰当的语言与他人沟通,发展人际交往能力。
3
共同解决情绪问题
当孩子遇到情绪问题时,父母需要尊重ta的情绪体验,和ta一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例如,父母可以这样对孩子说:“同学说你坏话,你感到很生气,打了他一拳。在这个时候,你感到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打人是不好的,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并且在此过程中,父母还可以给孩子提供调节情绪的策略。例如:“你感到生气的时候,尝试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然后再向老师寻求帮助。”
此外,也可以通过培养孩子的积极思维来提升孩子调节情绪的能力。情绪ABC理论认为,诱发性事件(activating event)是相对固定的,而不同的认知解释(也称信念,beliefs)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结果(consequence)。当孩子能用积极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他们遇到的事情时,就可以减少由不合理信念带来的情绪困扰。

例如:当孩子外出游玩却走错路时,ta可能感到着急或不满。但用积极的思维看待这件事,可以发现,虽然走错了路,但这条路的风景有不一样的美,享受意料之外的美景让人感到快乐和欣喜。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消极情绪一出现就要立刻去解决它。在某种程度上,消极情绪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适应性意义(任俊, 2006)。父母要做的是让孩子学会将消极情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4
调整自身的行为,做孩子情绪调节的榜样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更是孩子认识事物、探索世界的榜样。父母的情绪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
研究发现,在压力情境中,孩子会参照父母在相似情境中的调节策略来理解情绪事件的意义,并以相同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情绪表现(Silk et al., 2006)。一方面,父母积极调节自身情绪能给孩子树立适宜情绪体验、控制情绪表达等方面的榜样,从而促进孩子情绪调节的良好发展。

另一方面,情绪调节能力高的父母不仅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也善于有效应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情绪,由此营造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刘航 等, 2019)。家庭中积极情绪的表达有利于提高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而过多的消极情绪表达则会阻碍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Morris et al., 2007)。
情绪是天生的,但如何恰当地表达和调节情绪则需要后天的学习。在孩子成长的早期阶段,父母采取恰当的情绪教育策略不仅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发展情绪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而且教导过程中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也是亲子共同成长的难忘时光。
参考文献
刘航, 刘秀丽, 郭莹莹. (2019). 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机制与启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48–155.
任俊. (2006). 积极心理学 = Positive psychology.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叶光辉, 郑欣佩, 杨永端. (2005). 母亲的后设情绪理念对国小子女依附倾向的影响. 中华心理学刊, 47(2), 181–195.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6).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
Katz, L. F., & Windecker-Nelson, B. (2006). Domestic violence, emotion coach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 56–67.
Liang Z.-B., Zhang G.-Z., Chen H.-C., & Zhang P. (2013).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2), 199–210.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Myers, S. S., & Robinson, L. R. (2007). The Role of the Family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6(2), 361–388.
Silk, J. S., Shaw, D. S., Skuban, E. M., Oland, A. A., & Kovacs, M. (2006).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offspring of childhood-onset depressed moth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7(1), 69–78.
策划丨蔺秀云
撰稿丨张 琦
排版丨张昱凌
图源网络丨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