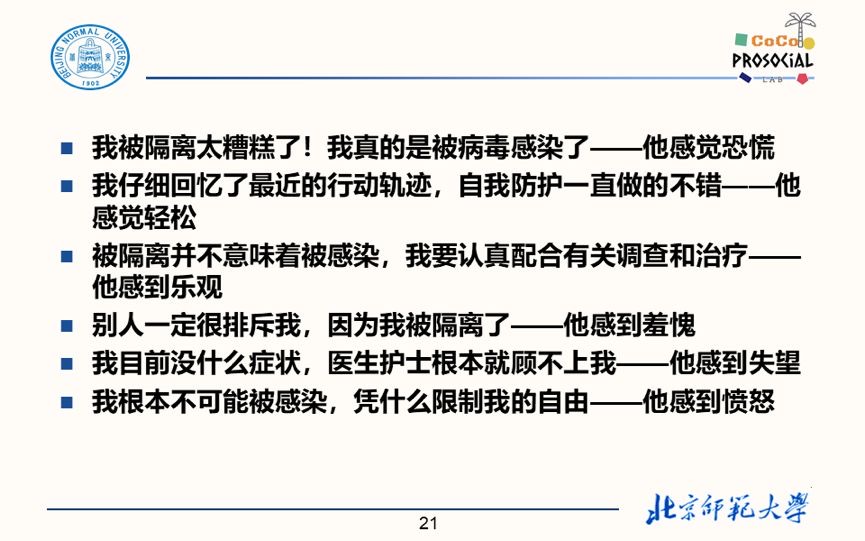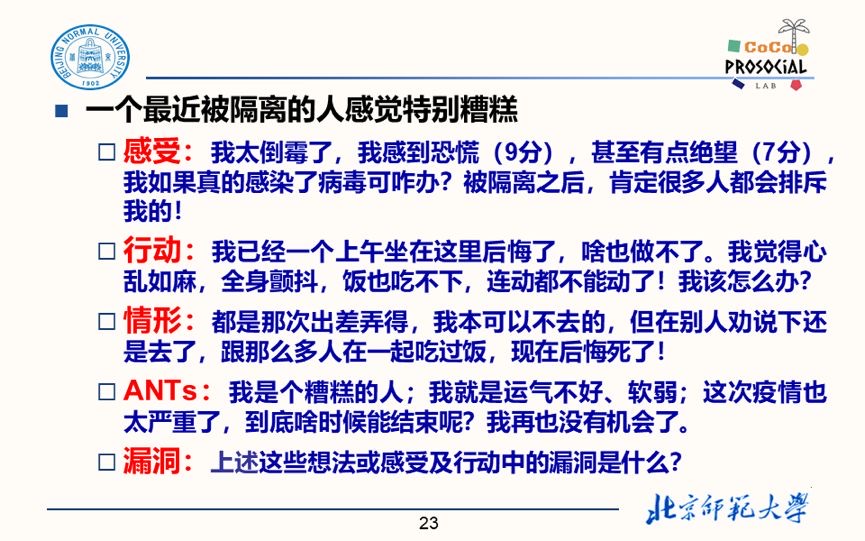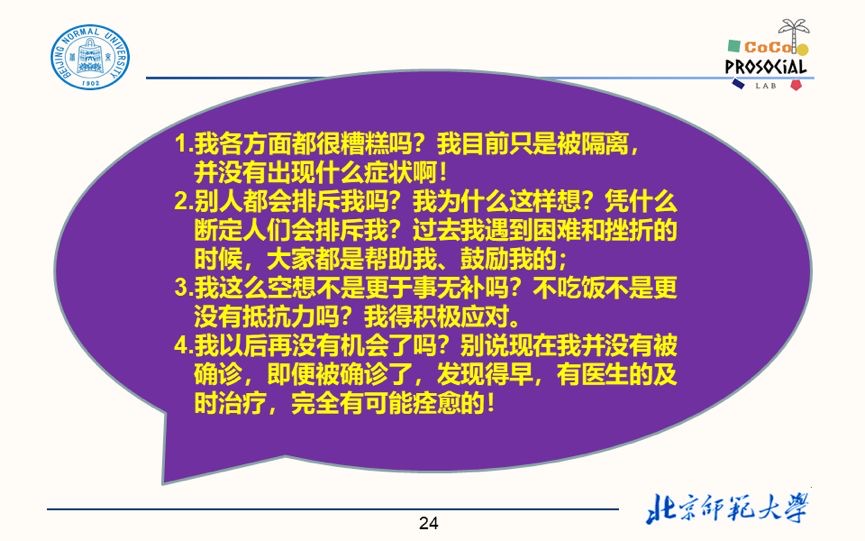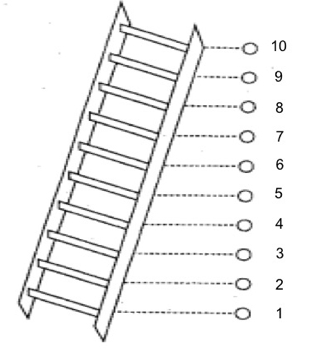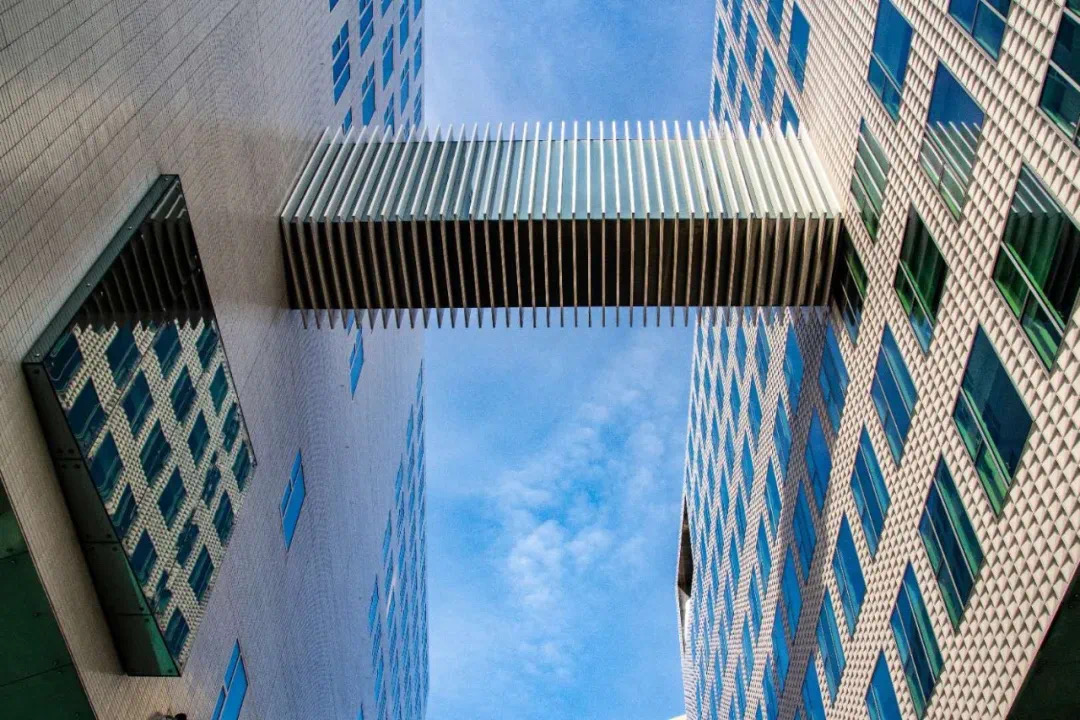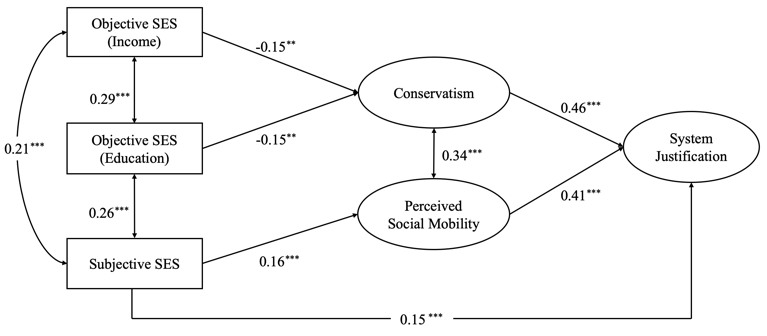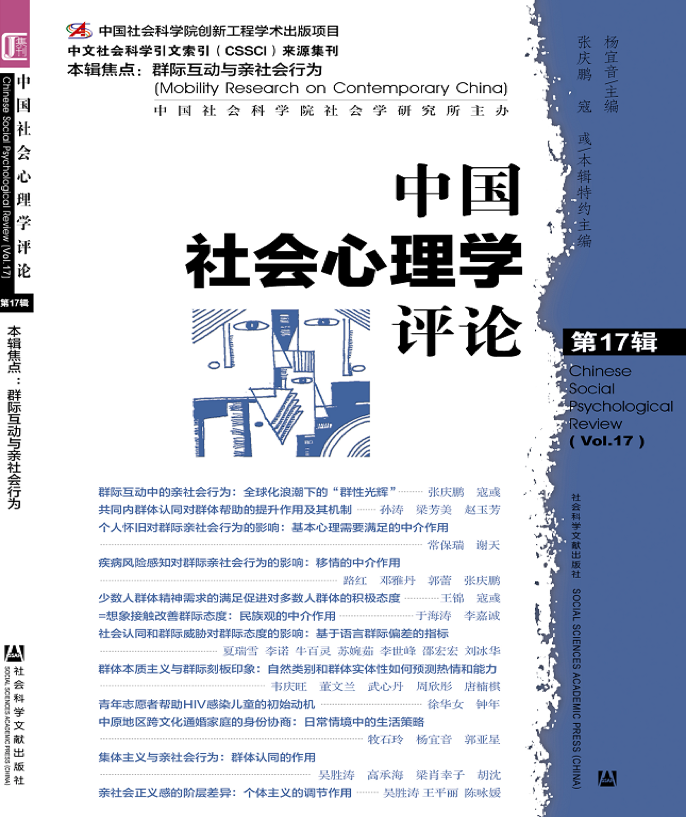亲社会实验室 | 挑食忌口影响社会生活吗?
文献选读
Coco有话说
民以食为天。食物不仅维系人的生存,也与情感相连。《舌尖上的中国》、《早餐中国》等美食记录片中,食物总是饱含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与积极的情感体验,比如过年的饺子和汤圆都寓意着“团圆”和“美满”。其实,食物也与朋友相联系,比如,“伙伴”这个词在古代就是指共灶饮食、同“火”的人们。可见,食物或者饮食方式,也可能与人的社会生活有关,挑食忌口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乃至情感体验。
此外,最近的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也可能与“吃”有关。所以,人们吃什么?怎样吃?实在是个“大”学问。
你有吃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吃的食物吗?微博曾评选出过这样的食物,香菜、鱼腥草、香椿等都曾出现在榜单中。有些人在食用某些食物时会伴随强烈的生理排斥反应,因此在他们的食物“黑名单”中,可能会有某些特殊的食物。有人可能因为乳糖不耐受而不能喝牛奶;有人可能因为不能吃辣而不愿和朋友一起吃川菜或湘菜;有人可能因为宗教信仰而避免食用肉类…….这些由于过敏、消化系统疾病、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原因,个体主动或被动限制吃某种或某些特定食物的现象,被称为食物限制(Food restriction)。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充裕,人们对食物的口味、材料、做法以及享用方式都越来越讲究,表现出的食物限制也越来越多。一项发表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认为,食物限制会引发个体的孤独感。
孤独感(Loneliness)是指个体因在现实生活中建立的社会联结水平未达到其所期望达到的社会联结水平而产生的消极情感体验,它分为情境性孤独感(Situational loneliness)和长期孤独感(Chronic loneliness)两种类型。情境性孤独感是一种相对短暂的、因缺乏社会联结而产生的消极体验;而长期孤独感是一种更稳定的状态,是由于个体多年来无法发展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造成的长期消极的孤独心境。

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发现,相比于没有食物限制的人,有食物限制的成人和儿童都会体验到更高的长期孤独感。
此外,研究者还采用实验操纵的方式设置食物受限制的情境(让假被试可以喝酒,而让真被试只能喝果汁)和食物不受限的情境(真、假被试都喝果汁),并比较这两种情境下真被试所体验的孤独感是否有差异。结果发现,被试在食物受限制的情境中体验的孤独感要明显更高。
那么为什么食物受限制就能使人感到孤独呢?研究者发现,这是因为食物焦虑的作用。食物焦虑(Food worries)是指食物受限制的个体在做出吃什么的决定时会花费太长时间,而这会使他们担心别人会避免和他们一起吃饭,或者会根据他们的食物选择偏好,对他们做出负面评价。也就是说,食物限制会引发个体的食物焦虑,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

研究者在实验室操纵被试回忆自己食物受限和不受限两种情境,发现被试只有在食物受限的情境中才会产生食物焦虑,而且随之就体验到了情境性孤独感。
研究者还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验证了这一现象。通过选取64名犹太被试,在逾越节(犹太教的节日)期间(食物限制的情境)和逾越节过后(食物不受限的情境),对被试感知到的情境性孤独进行前后两次测量,研究者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有趣的是,相比逾越节之后,在逾越节期间,食物受限制的犹太人,虽然确实感觉与非犹太人的联系更不紧密,但却感觉自己与其他犹太人(同样受到食物限制)的联系更为紧密。
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或被动面临食物限制的情境,在该情境中会体验到更高的孤独感,反复的食物限制经历也会让人们在生活中长期性地感受到孤独。
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1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食物在儿童形成和维系社会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孩子在选择吃什么的时候,会对来自家人和朋友产生的社会暗示很敏感,甚至会把由这种社会线索引发的孤独感延伸到成年期。例如,一个乳糖不耐受的孩子,在课间加餐时可能会因为父母的反复告诫而恐惧牛奶,因而无法与大家一同喝牛奶,他此时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情境性孤独。儿童如果反复经历这个过程,则有可能会形成长期孤独。因此,家长和老师应注意正确引导儿童,以防止食物受限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消极影响。

2
研究结果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强调了食物在文化中的作用。文化可以将食物消费作为限制内群体成员的信号,通过影响人们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来建立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此外,人们在享受饮食限制加强内群体联结这一好处的同时,对饮食文化带来的消极体验也应多加关注,避免自己和群体中其他成员因食物限制产生孤独感。
3
虽然本研究表明食物限制会提高个体感知的孤独感,但这种消极影响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在饭桌上,那些公开表达他们食物限制的人比那些隐藏自己食物限制的人,常常对于社会接受自己的饮食习惯更有信心,他们就不会对来自他人的信息过于敏感而产生孤独感。另外,食物限制也可能会通过彰显个体的独特身份而使其受益,例如,聚餐时宣称不能喝酒的个体往往还会得到他人的格外照顾;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原因而主动选择食物限制的人,也会因为其价值观或信仰而得到他人的尊重。

4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源头尚未查清,多地都贴出了“请居民不要购买活禽、野味”的告示。这种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食物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警醒人们理性看待饮食上的“猎奇”本质。但是,饮食方式突然改变可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消极情感体验。所以,有关部门也要关注人们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Woolley, K., Fishbach, A., & Wang, R. M. (2019). Food Restri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dx.doi.org/10.1037/pspi0000223.
推文作者:胡月琴
修改:郭震 林靓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本文由亲社会实验室原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征得作者同意后方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