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期末了,又一波厌学拒学高潮即将来袭……
作者介绍:周含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博士在读生
一位关注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的家庭治疗师
临近期末的前一个月,是全国各地家庭治疗师最忙碌的月份之一,前来求助的问题中,最让家长苦恼的问题莫过于:孩子拒绝去上学。
由于学业是儿童青少年阶段最主要的发展任务,学生拒学的行为,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突然不去工作了,两者都是社会功能出现严重问题的体现。
而且,让家长更为焦虑和担忧的是,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和技术不断迭代,许多低技能工作纷纷被淘汰,未来的职业和工作更加需要高新技术人才,这意味着自家孩子“拒学”行为如果持续,可能导致孩子在未来社会中没有竞争优势。

拒学是在校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影响。世界范围内拒学行为发生率在1%-5%之间 (Park et al., 2015)。
例如,Havik等人 (2015)对5465名11-15岁学生进行了大样本的测量,发现每个班级中约有一个孩子(约4%) 因拒学问题缺勤。
拒学现象本身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我国因拒学行为导致的就医和需要心理咨询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朱丽 等, 2019)。
那为什么孩子会拒学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01
拒学的定义和特点
探讨原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拒学。拒学行为 (school refusal,SR)指在儿童青少年自己不愿意去上学或不愿在学校呆一整天。Heyne等人(2011)提出了一个有效鉴别拒学的经典标准,如下:
1、上学困难,长时间地缺勤:过去两周出勤率低于80% (不包括合理理由的缺勤,比如需要做手术等);
2、严重的情绪不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症状:面临上学时会过度恐惧、发脾气、痛苦或抱怨、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出现躯体反应,比如胃痛、头晕、头疼,但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
3、上学期间,孩子在父母知情的情况下呆在家里,即家长知道孩子的去向;
4、没有同时出现的DSM-IV品行障碍,比如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性行为;
5、家长明确承诺孩子可以全勤上学,即父母希望孩子去上学,而不是留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打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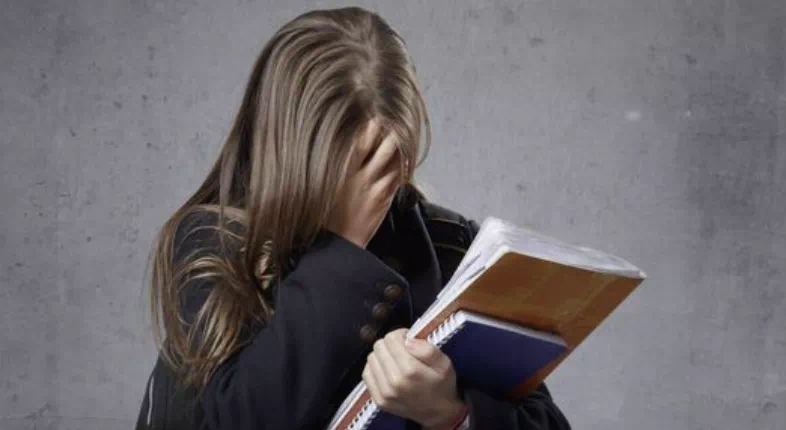
拒学与逃学(Truancy)的概念不同,逃学的孩子不太可能对上学过度焦虑或害怕。他们的缺勤更有可能是因为对学业缺乏兴趣,想参与更有吸引力的娱乐活动,以及不愿意遵从学校的要求和行为准则。
而且与“拒学者”不同的是,“逃学者”经常试图向父母隐瞒自己的缺课,并在其他反社会的同伴的陪同下从事违法和破坏行为。
此外,如果是父母积极鼓励孩子旷课导致的缺勤(例如,让孩子留在家承担照看弟弟妹妹或者病人的责任)也被认为是逃学,而不是拒学。
尽管较小比例的缺勤学生同时表现出“逃学者”和“拒学者”的特征,但是帮助这两类儿童青少年的方法有很大差别 (Berg, 2002),本文的重点将放在那些符合“拒学”标准的儿童青少年上。
02
厌学的原因
当一个孩子上学有困难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国内外对拒学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科学家们发现拒学的原因包括两大方面,分别是:
1
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
焦虑的来源有几个方面:
(1)与照顾者的分离焦虑。分离焦虑是导致儿童拒学的常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3/4左右患有分离焦虑症的儿童都有过拒学的经历 (Hella & Bernstein, 2012)。
最初的观点认为分离焦虑可以解释几乎所有拒学问题的原因,但是随着研究深入,这一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了。
因为“分离焦虑”这一解释低估了学校因素的影响,而且无法解释为什么拒学的高峰年龄在11至13岁之间 (Elliott & Place, 2019),因为按照分离焦虑的解释,拒学问题的高峰应该出现在6岁左右。

(2)学校环境中负性事件或负性体验。学校里的负性事件或体验是拒学的重要因素,也是焦虑的主要来源 (Knollman et al., 2010)。
一方面,学校是经常需要社交的环境,包括当众演讲、朗诵和上课回答问题,拒学很可能是社交焦虑导致的 (Beidel, 1998)。
另一方面,学校经常会对学生进行各种评价,包括各种随堂测试、考试、教师反馈等,对评价恐惧的学生也会导致他们害怕上学 (Havik et al., 2015)。
(3)学业压力。学业压力通常会因重要考试(比如,期末考、中考、高考)而加剧,各种重要且难度高的考试通常会导致难以忍受的高度焦虑(Connor, 2003; Denscombe, 2000; Putwain, 2007)。

(4)消极的同伴经历。消极的同伴经历包括被同学排挤或者欺负,有的学生还需要应对“偏见欺凌”,即因为性取向、信仰和残疾等原因被边缘化 (Walton, 2017)。
(5)学校教职工的态度。Torrens Armstrong等人(2011) 调查了学校教职工对拒学学生的评价,发现他们会对拒学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指责,并且认同遭受欺负的合法性,即认为学生时代或多或少会遭受欺负,这是不可避免和控制的。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学校教职工的这些理念对接下来拒学学生行为的改变有何影响,但是可以预料到,如果学校职工认为学生遭受欺负以及拒学是他们无法管控的事情,那么他们也不会在住宿、座位安排等方面特殊关照这些学生。
因此,评估不仅要确定拒绝背后的原因,还要考虑学校工作人员对这些原因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支持和帮助拒学孩子的意愿。
2
拒学会带来一些好处
拒学的第二大类原因,是拒绝有一定的功能性,包括:
(1)回避负面情绪,通常是回避某些特定的恐惧;
(2)逃离负性社交和评价环境;
(3)获得照顾者的关注;
(4)寻求校园之外的强化。
当然,孩子拒绝上学可能经常带来重叠功能。为了更加详细和细致的了解,专业人员在评估时可以使用拒学量表作为工具,辅以访谈和观察,以及尽量获取来自家长、教师和儿童青少年等多来源的信息。
03
怎么应对?如何干预?
干预的首要目标是减少拒学孩子的情绪困扰和增加学校出勤率,这些能帮助他们走上正常的发展路径。
但由于拒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且因个人而异,Elliott和Place (2012)指出,“拒学”甚至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身体问题或者学习功能不足)的附带症状。
因此,在进行干预之前,家长和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先对拒学背后的可能原因进行仔细的评估和筛查,避免误判。

在进行初步评估时,首先要确认与焦虑相关的躯体症状(如心悸或胃痛),是否是因为身体问题引起的,因此,先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是有必要的。
其次,需要对拒学孩子的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因为学习功能不足(比如,上课听不懂,不会做题,跟不上老师进度)是很多拒学孩子经常抱怨学校的地方 (Fernando & Perera, 2012)。
智力评估,特别是语言能力评估,将有助于接下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帮助拒学的孩子。
第三,对孩子的认知思维模式进行详细的了解是很重要的。例如,有证据表明,拒学的孩子更有可能对失败抱有悲观的想法,比如某一次或几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觉得自己很笨 (Place, Hulsmeier, Davis, & Taylor, 2000, 2002),这可能会削弱他们应对困难时的自我效能感。
目前常见的疗法包括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短期焦点治疗和药物治疗等,根据个人需要,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其中,最受欢迎的方法仍然是认知行为治疗,以往研究也建议认知行为疗法结合家庭治疗和药物治疗。总之,许多治疗方法都关注家庭和学校中可能增加或减轻焦虑的环境因素。
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 (CBT)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拒学问题的首选治疗方法(Elliott & Place, 2019)。CBT通常结合了心理教育、放松训练、社交技能训练、系统脱敏和认知重构等方法。
在最近的一系列综述中,发现CBT确实可以有效地缓解儿童青少年的一系列焦虑症状 (Higa-McMillan et al., 2016)。
Reissner、Hebebrand和Knollmann (2015)开发了一种基于治疗手册的、多模式治疗方法,包括四个模块,其中最重要的模块是使用认知行为疗法,专门解决拒学问题,其余三个模块的重点分别是家庭治疗、与学校有关的辅导和提供具体策略,以协助儿童在社会和其他环境中更有效地应对困难。
Walter等人(2010)对长期缺课的焦虑抑郁青少年采用了CBT疗法,辅以家庭工作、住院患者支持(包括逐步脱敏和有效利用休闲时间的培训),发现干预效果良好:被干预的孩子出勤率显著提高,共病的心理健康问题显著减少。
2
家庭治疗
在制定干预计划时,家庭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Berg (1992)的研究观察到,只有当孩子真的意识到父母希望他们回归学校时,才会逐渐恢复正常上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和学校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Doobay, 2008)。
许多父母试图将孩子的困难归咎于学校,但孩子的拒学与家庭环境的高压和焦虑也是密不可分的。重要的是,学校的改变很少能解决问题。
当面对自己的孩子苦苦哀求、且高度痛苦的样子,父母通常需要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来维持一个“坚定的、有同情心的、但没有商量余地” 的立场,即充分地理解和共情孩子的痛苦,但是依旧坚定地要求他们回到学校的立场。

Kearney和Silverman (1995)描述五种经常出现孩子拒学的家庭类型,包括:家长很强势又很多冲突的家庭、彼此之间过度依赖和缠结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没有互动的家庭、与家庭外的团体或组织互动很少的家庭、孩子有精神类疾病的健康家庭。
他们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家庭将需要不同形式的家庭治疗干预,干预重点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需要视情况而定。
虽然家庭疗法长期以来一直被提倡用于治疗拒学问题 (Bryce & Baird, 1986; Richardson, 2016),但是很少单独地使用家庭治疗这一个方法干预,目前针对家庭关系的干预工作通常嵌入在CBT计划中(Heyne et al., 2014; Reissner et al., 2015)。
3
药物治疗
拒学问题的药物治疗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调查服药对儿童青少年拒学问题的作用,因此也无法得知药物治疗对解决拒学问题的准确作用。
但以往研究已经证明药物治疗对于治疗焦虑症有很明显的作用(Ipser, Stein, Hawkridge, & Hoppe, 2009),抗焦虑药物的临床效果明显大于安慰剂药物。
选择性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因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焦虑症的首选药物治疗方法。
其他药物如三环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镇定剂(anxiolytics)、肾上腺素α受体激动剂(alpha-adrenergic agonists)和肾上腺素能阻滞剂(beta-adrenergic blocking agents)也被使用。
总之,对拒学的定义、原因和已有治疗方案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后可以发现,拒学是一个全世界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难题,对拒学的干预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进行充分评估后进行多方法的干预。
对拒学问题的干预研究中发现,无论采用何种干预方法,对年龄较小的儿童更为有效 (Prabhuswamy, Srinath, Girimaji, & Seshadri, 2007; Valles & Oddy, 1984)。
有几个因素可能导致干预大一点的孩子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拒学的青少年往往比年幼的孩子有更强的自主意识和自主权利,这导致他们拒绝大人的约束;
二是青少年时期的学业任务难度更大,在非常重要且难度高的考试临近时,拒学的青少年要重返学校去面对更复杂、要求更高、更专业的课程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拒学的青少年在校期间往往会经历更严重的症状 (Hella & Bernstein, 2012; Heyne, Sauter, Ollendick, van Widenfelt, & Westenberg, 2014)。
参考文献
朱丽,程丽,张免,郑明明 & 朱囡囡.(2019).家庭治疗改善青少年拒学行为效果分析.中国学校卫生(03), 396-398.
Beidel, D.C. (1998).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Etiology and early clinical present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59 (Suppl. 17), 27–32.
Berg, I. (2002). School avoidance, school phobia, and truancy. In M. Lewis (Ed.),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pp. 1260–1266). Sydney, NSW: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Bryce, G., & Baird, D. (1986). Precipitating a crisis: Family therapy and adolescent school refuse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 199–213.
Connor, M.J. (2003). Pupil stress and standard assessment tests (SATS): An update.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 8, 101–107.
Denscombe, M. (2000). Social conditions for stress: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 of doing GCSEs.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6, 359–374.
Doobay, A.F. (2008). Scholl refusal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A 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 to treatment.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5, 261–272.
Elliott, J.G. (1999). School refusal: Issues of conceptualisa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0, 1001–1012.
Elliott, J.G., & Place M. (2019). Practitioner Review: School refusal: developments in conceptualisation and treatment since 2000.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60 (1), 4–15.
Fernando, S.M., & Perera, H. (2012). School Refusal: Behavioural and diagnostic profiles of a clinical sample. Sri Lanka Journal of Psychiatry, 3, 10–13.
Havik, T., Bru, E., & Ertesvag, S.K. (2015). Schoo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chool refusal- and truancy-related reasons for school non-attendance.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 221–240.
Hella, B., & Bernstein, G.A. (2012). Panic disorder and school refus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1, 593–606.
Heyne, D.A., Sauter, F.M., & Maynard, B.R. (2015).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of treatments for youth with school refusal or truancy. In M. Maric, P.J.M. Prins, & T.H. Ollendick (Eds.),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of youth treatment outcomes (pp. 230–2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yne, D.A., Sauter, F.M., Ollendick, T.H., van Widenfelt, B.M., & Westenberg, P.M. (2014). Developmentally sensitiv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dolescent school refusal: Rationale and case illustratio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7, 191–215.
Heyne, D.A., Sauter, F.M., van Widenfelt, B.M., Vermeiren, R., & Westenberg, P.M. (2011). School refusal and anxiety in adolescence: Non-randomized trial of a developmentally sensitiv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5, 870–878.
Higa-McMillan, C.K., Francis, S.E., Rith-Najarian, L., & Chorpita, B.F. (2016). Evidence base update: 50 years of research on treatment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anxiet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5, 91–113.
Ipser, J.C., Stein, D.J., Hawkridge, S., & Hoppe, L. (2009). Pharmaco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3), CD005170.
Kearney, C. A., & Silverman, W. K. (1995). Family environment of youngsters with school refusal behavior: A synopsis with implications for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3, 59–72.
Knollman, M., Knoll, S., Reissner, V., Metzelaars, J., & Hebebrand, J. (2010). School avoida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Deutsches Arzteblatt International, 107, 43–49.
Ollendick (Eds.),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of youth treatment outcomes (pp. 230–2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k M.H., Yimhw, H.W., Park, et al.. (2015) School refusal behavior in South Korean first graders: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mmunity-based study[J]. Psychiatr Res, 227(2/3), 160-165.
Place, M., Hulsmeier, J., Davis, S., & Taylor, E. (2000). School refusal: A changing problem which requires a change of approach?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 345–355.
Place, M., Hulsmeier, J., Davis, S., & Taylor, E. (2002). The coping mechanisms of children with school refus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2, 2–10.
Putwain, D.W. (2007). Test anxiety in UK schoolchildren: Prevalence and demographic pattern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7, 579–593.
Reissner, V., Hebebrand, J., & Knollmann, M. (Eds.) (2015). Multimodale Interventionen f€ ur psychisch belastete Schulver-meider-das Essener Manual. Stuttgart, Germany: Kohlhammer.
Richardson, K. (2016). Family therap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school refusa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7, 528–546.
Walter, D., Hautmann, C., Rizk, S., Petermann, M., Minkus, J., Sinzig, J., ... & Doepner, M. (2010). Short term effects of inpatient cognitive behavioral treatment of adolescents with anxious-depressed school absenteeism: An observational study. Europea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 835–844.
撰 稿:周含芳
责 编:高文洁
美 编:何文宣
图 源 | pinterest,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