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实验室 | 群际互动中的亲社会行为
好书推荐
Coco有话说
在国内外社会多重流动的背景下,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社会规范、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而出现了类型众多的社群或团体。这些群体在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文化互动现实,并对社会心态和社会行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7辑的十一篇论文聚焦于“群际互动与亲社会行为”这一主题,从群际接触、群际助人、群体认同、群际高级社会情感乃至于更抽象的群际认知哲学等角度出发,尝试揭开群际感知背后精微的社会心理内涵和复杂的文化经验根系,为提升群际融合品质找到新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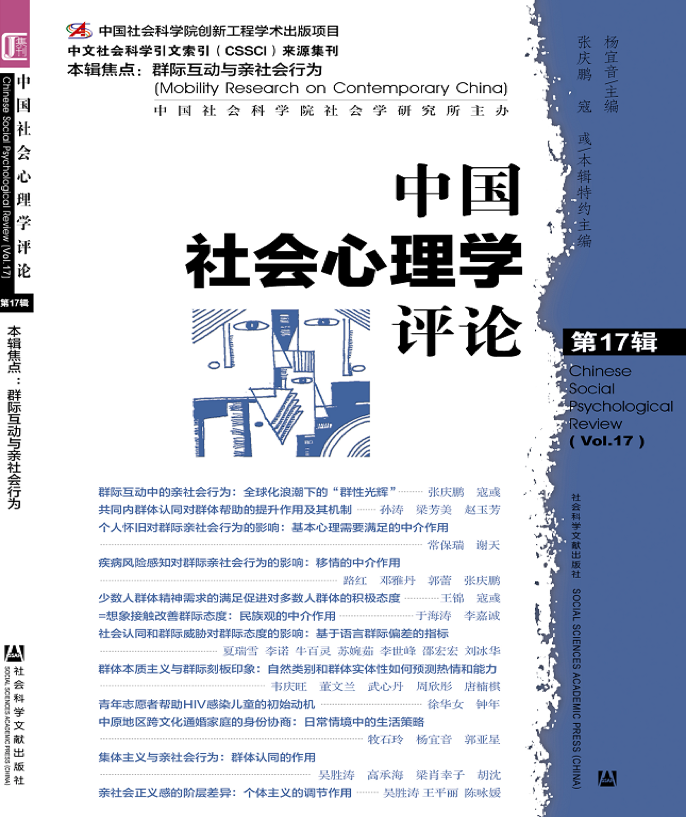
为什么要研究群际亲社会行为?
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语境下,多重流动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重叠,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社会文化互动现实。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资源流动和人员流动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类型越来越多,新型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多变的过程,这就使得基于群体间接触和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成员针对“外群体及外群体成员”的心理表征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特征。在国内流动/跨国流动的群际互动框架内,本地人基于针对外地人/外国人群体的观感和接触,对这些城市新移民身份的积极印象或污名感知,会以想象、隐喻或代表性符号的方式透过传媒和人际沟通的渠道最终生成特定的社会表征模型,进而深化并巩固成为共识性的大众经验。
这一整套始终处在动态调整中的群际互动经验是在社会流动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社会群体多元并存的外部现实、以及在心理表征和人际互构的内部过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内外因素促成的社会共识对其持有者产生了规范性影响,进而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群际互动的过程既复杂又多变,据此建立的各类群际关系也呈现出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形态,并展现出迥然不同的价值对照关系,包括在外显意愿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对照内隐认知层面上的消极偏见,以及在积极的外群体态度背后对照内群体规范认同逻辑。这就使得“如何整合外显态度与内隐认知、如何整合内群体规范与跨群体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群际和谐”成为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这也是本专辑聚焦于“群际亲社会行为”的缘起和初衷。

群际互动的过程隐含了不同规范、习俗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同时也折射出了不同群体之间由于权力和地位的差别而出现的合作、冲突或博弈,此外还有这些群体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所激荡出来的创意和智慧。上述内容背后的建设性内涵(比如群体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和良性互动)和破坏性内涵(比如群际偏见、歧视甚至冲突)是并存的,对于建设性内涵的培育和促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群际互动中的破坏性内涵。
在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移民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关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解释模型和干预机制可以为探索群际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在传统的个体主义心理学范式下,亲社会行为被界定为发生在个体之间具有利他属性的、旨在提升人际关系并通过巩固规范和强化习俗来促进内群体和谐的积极行动。从概念的原型结构来看,人际互动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既涉及到特质性、利他性和社交性等自我/个体心理特征,同时也涉及到诸如遵守群体规范/维护社会公益这样的群体心理特征(张庆鹏,寇彧,2011),它一方面促进了积极自我概念的建立和良性人际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些改善的不断积累也潜在地推动了积极社会共识的形成,最终建立稳定的亲社会规范,成为建立成熟社会的核心基础。这表明亲社会行为是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也是在内群体规范认同和跨群体社会互动之间建立积极联系的粘合剂。
如果将人际社交层面上的“亲社会”的理念切入到群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则可以将个体心理层面上的亲社会动机和心理行为模式拓展到群际互动层面,并提炼出“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一概念。群际亲社会行为在表象层面上依然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具有友好、合作、分享和互助等特征的积极行动,但形式上的人际行为隐含了群际互动的意蕴,由于身兼不同群体身份的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时也各自稳定地拥有相应的身份认同,这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内核层面上成为基于个体身份认同的群体间行动。我们可以透过群际亲社会行为来分析变迁背景下的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群际互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由此结成的各种关系,进而探索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中消解偏见与歧视、促进群际和谐与族群融合,呼应“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网”、“世界朋友圈”等议题。
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社群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频繁的接触(包括跨国贸易、跨境留学、跨境就业甚至跨国通婚等),基于“亲社会”构造起来的建设性的群际互动内涵对于这种多元复杂的接触过程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不止体现于消除偏见和化解冲突(或者通过冲突来协调各方面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平衡社会的功能),而且还体现于重塑共识和提升融合品质,并实现更为深刻的文化整合。可见,在这方面所开展的研究正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日益成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领域。

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积极群体关系表征下的良性社会互动
我们可以将基于群际亲社会行为建立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不同群体成员通过社会表征建构出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联结/关系”。与个体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相比,群际亲社会行为涉及到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以及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关系,因而是在多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中发生的社会互动,也就必然需要以人群中业已形成的普遍共识或集体社会表征为基础。就群际亲社会行动中的当事双方而言,关系表征的影响因素以及运行机制更多地反映了群体之间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对话与博弈,这些议题涉及到双方在“施助-受助”或“互助”的过程中进行帮助、合作、分享等亲社会互动时,制约或影响他们行为的规范是如何建立的。而这些规范一旦建立之后,随之出现两种典型的亲社会群际关系。
第一种是依赖定向关系(dependency-oriented relationship),施助者强调内外群体的差别和内群体的独特性,通过为受助者提供直接的问题解决方案,借以稳定或扩大群际阶层差异,进而获得受助者的长期依赖,因此虽然表面上是积极的,其实质却是为解决群际威胁的“亲-内群体(pro-ingroup)”行为,其中不乏针对外群体的控制、排斥等消极互动,而该取向下的求助者则将求助情境归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所致。这种关系反映了群际互动过程中的负面要素(张兰鸽等,2015)。
第二种是自主定向关系(autonomy-oriented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框架内的群际助人行为涉及“自主独立性”、“求同包容性”等核心特征,施助者强调群际共性,可以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多样性,通过为受助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去尊重后者的自主价值及独立尊严,试图在利他主义框架内缩小阶层差异,并与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产生正向联系,最终建立起良性的群际关系。该取向下的求助者则会基于求助情境产生较强的动机去解决当前的技术性问题(张兰鸽等,2015)。因此,自主定向的群际亲社会行为具备了更多的建设性内涵。自主定向关系反映了群际互动过程中的正面要素。比如在解决诸如利益分配、责任分担和冲突解决等问题时,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平等协商,并且都可以接受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出各自妥协的方案。建设性群际关系一方面更容易促进群体之间基于其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激荡出创意和智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建立积极而稳定的群际关系,实现良性的社会建构,避免出现由于偏见、歧视、攻击等冲突所引发的破坏性局面。
亲社会群际互动中的依赖型关系和自主型关系都是在人们对于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相对阶层位置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感知、表征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群际互动的语境下,差异性表征的激活使得同样的助人场景背后隐含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价值诉求。很明显,依赖定向较容易引发群际偏见、敌对甚至冲突,而自主定向则更倾向于对应友善合作的良性互动,后者在本质上具备了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内涵,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际融合。
因此,后续关于群际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应着眼于其中的“自主性”内涵展开深入探讨,比如从自我认知、社会表征、社交性情绪/情感以及群体规范等角度出发去探讨其影响因素,再比如从基于群际接触、文化学习、多样性表征训练以及交叉认同分类训练等角度去促进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基于会聚主义文化心理机制的群际亲社会互动
在国内流动和跨境流动的双重作用下,当代中国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交融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林林总总的群体类型,随之也制造出了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议题。群际亲社会行为作为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蕴含于行动背后的积极要素折射出了全球化浪潮下的群性光辉,并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揭示出多种文化互动场景下推动群际合作或消减群际冲突的底层逻辑。
为了阐明这种“揭示”的内涵,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当代多群体交互现实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在多重流动和跨文化碰撞等复杂社会现实的交织下,无论是站在坚持内群体独特性的文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立场,还是站在强调无差别群际平等的文化色盲主义(colorblindness)立场,甚或是站在既接受多样性又鼓励自由表达与行动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立场,都很难完整并准确地判断群际互动的本质和成效(邹智敏,江叶诗,2015)。
因为群际互动中多种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兼具多样性和整合性的内涵,这种内涵可以借助于影响源的叠加性特征和影响过程的多重性特征来加以理解。某种文化基于特定的侧面(而不是全部要素)对其成员产生影响,而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影响则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特定侧面,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是在多种文化会聚之后被塑造形成的(Morries,Chiu & Liu,2015)。这就促成了几种风貌与内涵皆存在差异的群体形态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场域之内,伴随着新群体的不断出现,行为主体存储的社会与文化知识涵盖了两套或多套文化系统,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吸收和相互转换的涵化(acculturation)关系,它们被整合在一起对社会行为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优化了上述三种立场背后的理论解释力,进而指向了最早由Prashad(2001)提出的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ism)理念。
文化会聚主义理念启发我们基于本文的阐述继续向深层的社会心理学议题空间拓展,进而将群际亲社会行为纳入到文化系统建构的动态进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对话、混搭和转换迭代的过程中会聚为全新的文化系统,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其中扮演了联结、凝聚与整合的角色。群际亲社会行为既可以为社会建设与文化重构过程中的跨群体互助、协调、提升与整合等议题提供道路选择或方法路径,在多元杂处的文化融合背景下揭示出两个或多个文化系统对群体行为的综合作用机制;还可以在群际互助的过程中探寻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文化、规范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对话与融合,梳理出积极群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和群际权力健康合理运作的原理。
本专辑收集了一组围绕“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个主题的系列研究论文,目的是在上述视角下探索群际互动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并为如何消除偏见、提升与改善群际关系提供实证依据。
本专辑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直接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例如赵玉芳团队以壮族和苗族大学生为被试,基于两个系列的实验发现了共同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帮助的提升作用,并且揭示了感知相似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谢天团队以慈善捐助为例,考察了“个人怀旧”在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对群际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路红团队采用博弈游戏范式,考察了感知到的疾病传染性与致死程度对群际亲社会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时验证了状态移情的中介作用。
第二类研究聚焦于群际互动过程中的态度和动机。例如寇彧团队的研究发现,少数人群体的内群体精神利益满足降低了外群体投射,继而促进了他们对多数人群体的积极态度;于海涛团队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三个系列研究探索了想象的群际接触对内隐群际态度的影响,并检验了民族观的中介作用;夏瑞雪团队的研究揭示了社会认同程度和群际威胁感知对不同民族间群际态度的交互影响;韦庆旺团队考察了群体本质主义的自然类别维度及群体实体性维度与群际刻板印象(能力-热情)的关系;徐华女团队则借助质性访谈的方法,深入挖掘了青年志愿者和艾滋病感染儿童之间的群际帮助行动背后的多重初始动机(如痛苦感知、感恩图报、追求正义等)。
第三类研究将亲社会行为置于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会聚主义的层面上,探讨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杨宜音团队深度描绘了中原民族散杂居地区的回汉通婚家庭日常生活场景,在社会距离最近的文化接触形态下讨论了婚内族际文化融合心理边界的特性;吴胜涛和高承海团队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族群异质性和差异性;吴胜涛团队的另一项研究则探讨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及其文化价值基础,发现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个体主义倾向调节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
心理学研究最大的价值应在于,当其理论贡献反照到社会现场之后可以发挥其阐释现实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功能。本专辑关于“社会群体”和“群际关系”的研究契合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继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宏观战略,同时也回应了“国家安全的基础管理”和“跨区域的系统性人口迁移治理”的现实需求,希望能够将不同类型的群际关系背后的生成机制和促进策略作为当前实现族群共生和文化共融的实践抓手,为建立和提升有关城乡社区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互动、跨文化和跨族裔间合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策略体系提供实践性参考。

注:本文部分节选自《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7辑:群际互动与亲社会行为》卷首文章《群际互动中的亲社会行为:全球化浪潮下的“群性光辉”》,本专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集刊主编:杨宜音,执行主编:张庆鹏,寇彧。
推文作者:张庆鹏
插图:郭震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本文由亲社会实验室原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征得作者同意后方可转载